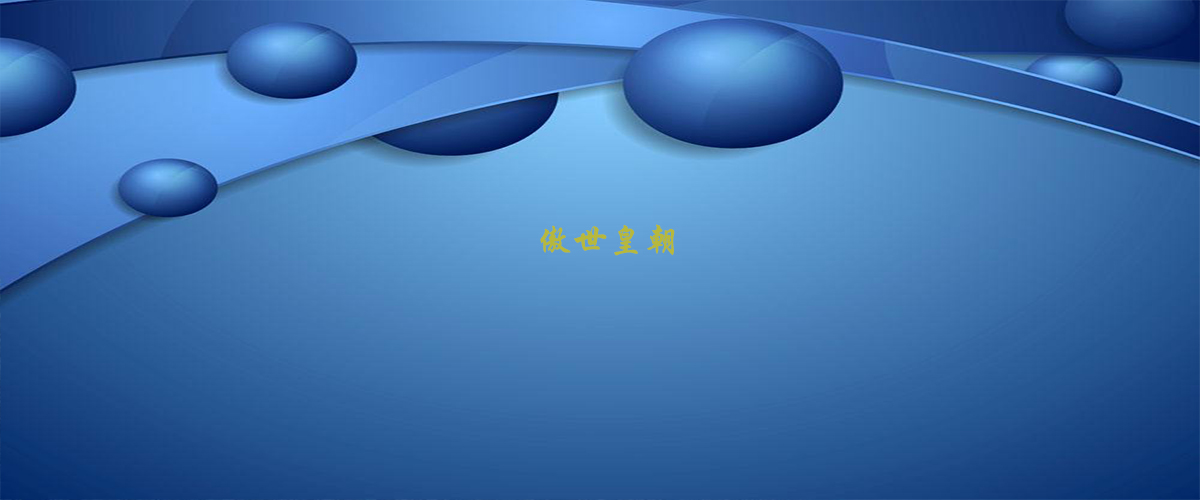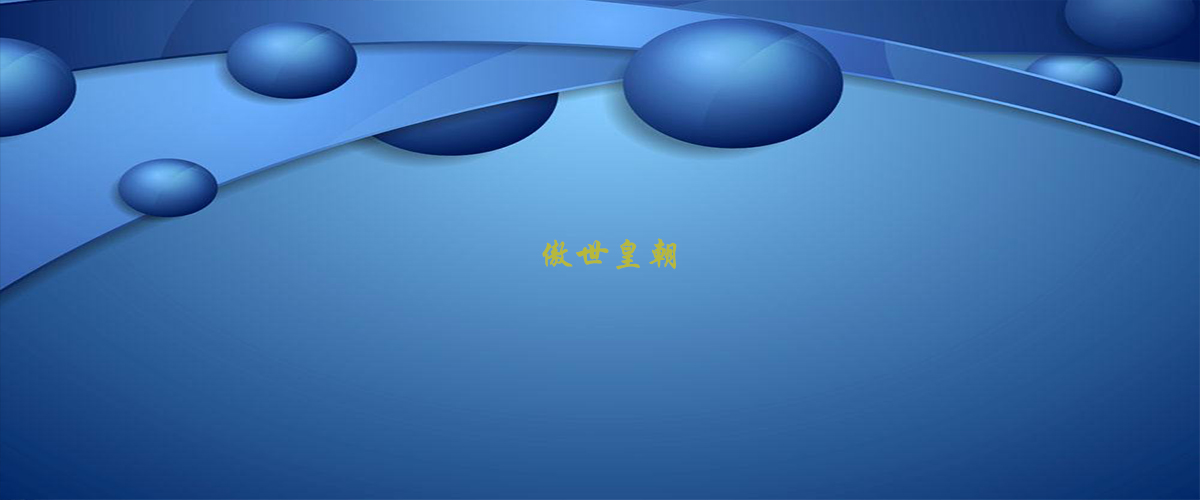傲世皇朝平台|《安徽文学》2022年第1期|耿立:替一颗苍耳活着(节选)
傲世皇朝娱乐平台登录发布:
一
有人从城市拿着柄斧头走向了乡野,建一木屋,受够了漂浮在城市上空的污浊云霾和那些噪声,宁肯一个人坐在一颗南瓜上,也不想挤在天鹅绒坐垫上。
但对一个乡下出生,乡下成长的人来说,城市对他意味什么?他又居于何处,又因何而生?
他能把城市当作一颗南瓜坐下吗?
如果将人分为乡下人、城里人、流浪者(漫游者),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从乡下到城里的流浪者,最后能成为一个城里人,这是内心的真实,即使像《红与黑》中的于连,这并不下贱,也不低俗。
当去澳门参加五四百年研讨会,看到那些百年的遗存和金碧辉煌的游乐场,恍惚间觉得我像一个苍耳附着在城市的墙上、树上。在座谈的时候,我意识到,我就是一颗苍耳,虽然有着光荣的刺,但要谦卑,这是城市,城市里的水泥地面是没有多少苍耳生存空间的,在乡土上,你好像很强大,那些刺,一是针对伤害你的人的,二则是一种附着借力的武器,到远方去。
作为一个苍耳,我是多么渴望踏进城市、落脚城市,虽然我在与澳门一水之隔的珠海,虽然在珠海之前,我在鲁西南一个地市级的小城,但就是在那样的小城,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居留,我依然是那么的虚弱,不敢像在乡土上,把刺亮出,只能把那刺攥在手心里软化。
是的,苍耳的刺,是可以被手心的手汗慢慢浸软,慢慢失掉骨头,像一面投降的旗子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我在鲁西南小城毕业留校的时候,我一无所有,拥有的只是年轻和热血,但热血有用吗?
“你以为你是谁?”这个声音多次在我的耳边响起,就像苍耳的刺,直直地扎向我,即使扎我的肉,扎出血,我也必须忍着。我知道,我是一个从乡间来到城里的苍耳,苍耳在城里没亲戚,没朋友,那些草都被赶到城市的边缘,我要留下来,活着。
那天,一次小范围的聚餐。一个不是同一专业,高一年级的学兄,留校做了某个系的团总支书记和辅导员,对学生、对同僚,跋扈;对上级,又驯服、谦卑,常去领导家干杂活,通下水道、打扫厕所,最拿手的是,做的一手好鲁菜,领导家每次来人,他必下厨展现刀工,能把土豆切成发丝,在客人面前展现烹煎炸炒汆。
那天因感冒,我勉强坐在酒桌前,一直打哈欠、咳嗽,还不到晚上九点,但因是冬天,天黑的很透,就盼着早早结束,在喝酒举杯的时候,说明了原因,大家谅解了,喝酒减半。但到这个学兄所谓的“走一圈”,和每人都喝酒时,我说,感冒了,喝一半,就喝了一半,然后他就给我剩下半杯的酒杯重新斟满。
喝下,我们不许喝半杯!
感冒了。
感冒?谁没感冒过?
我……
什么我我我的,你以为你是谁?
我陡然从头顶听到这样一句横空劈来,这么跋扈刺耳的声音,也像苍耳之刺,那么不容置疑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你喝不喝?
我感冒了,不要强人所难。
什么强人所难,这么文绉绉的,酸得倒牙。
这时他暴风急雨、乌云压城,好像我不喝下这杯酒,就是折了他的权威,驳了他的面子,伤了他的自尊。
你以为你是谁?你以为会写个狗屁文章,就牛逼了,没门!
他说着,就把那整整一杯酒,浇在我的脖颈里,正感冒发烧,皮肤滚烫,那一杯酒就如冰块,或者是我的身体就如一块火红的铁,一下子就被酒淬火,就觉得浑身冒白烟。
我是谁呢?我一下子想到于连,这是从高中就落脚我心灵的人物,但我不是于连,少了他的狠,他只是滋养我的精神。我只是一个无根基的才留校、嘴上无毛才二十出头的农村孩子,这一杯侮辱的酒应该激起我的血性,也把一杯酒泼在他的脸上。但我知道,明天,我可能会卷起铺盖走人滚蛋,苍耳,有刺,但这刺,是为了更好的生存,附着,而不是刺人,我知道,苍耳毕竟是草。
大家看学兄把一杯酒浇在我的脖子里,似乎是看笑话,看我的反应。我说,他喝多了,能理解。
这是最无力,给自己找台阶下的一句无奈的话。但这是弱者和炮灰的话,是人的遁词。
活着,把苍耳的刺往里长吧,毕竟是草。
乡下人像草,匍匐着长,在夹缝里长,它们低贱、卑微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我曾多次写过黄壤深处的草,一本散文集名字就叫《藏在草间》,但都是说乡亲父老如草一样卑微,一样低贱,他们不霸道不欺负人,写老父亲对草的感情甚于粮食,他的素朴哲学七分种草三分种粮,给自己、给鸟儿、给牛羊留口吃的,父亲算得很清晰,一年到头,该给自己多少口粮,剩余的植物动物也不能亏待。庄稼是草本的,人是草命的,仿佛人与这些植物都是DNA相同的兄弟。
但我想,如果我是一棵乡间的草,我该是什么呢?节节草?萋萋芽?嘎巴草?婆婆丁、马齿苋、扫帚菜、败酱草、牛舌头棵?不。
我是一颗苍耳。我就是一颗苍耳。
多像乡间的这植物,苍耳,是的。这粒种子,想方设法附着、粘在路过乡间的羊毛上,牛的肩胛上,动物的腿上、尾巴上、身上,人的衣服上、裤脚上。
这是多么倔强的植物,很多人不喜欢。在乡间,你一定见过它,它的坚韧、顽强,不肯罢休的性格,只有把它碾成齑粉,否则,给它一丁点的土,它就会活下去。
我总觉得,这是一个噙着泪,哭泣着走的植物,值得敬礼的植物。它类似一类乡下人,这就是生活本身的符号,正如朱娜·巴恩斯所说,“我所描绘和勾勒的生活就是生活本身”,但“正因如此你说它是病态的” 。
苍耳的执着,被人认为病态,但这是把故乡带在身上的植物,固执的植物,是个会移民的植物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萨尔曼·拉什迪说:“我们都在越过边界,所有人都是移民。从美国农村到纽约市,是一种远比从孟买迁往纽约的更极端的移民行为。在这个漫游的世纪里,流亡者、难民、移民在他们的铺盖里装着很多故乡。”
乡下有很多的草,这是人世间和植物里最低贱的品类,但生生不灭的是它们,在田间、在沟旁、在水渠、在屋顶、在墙垛,凡是有一丁点土的地方,就有它们,你践踏它、责骂它,用铲子镰刀,甚至放火,也灭不了它。
我曾想编写一个乡下的草词典,比如——
萋萋芽:学名小蓟,多刺如锯齿,鼻子冒血,弄几枚叶子挤烂,塞到鼻孔里,血立马就止。
马蜂菜:别名马齿苋,叶片团团厚厚,油油的,肉乎乎的,它的茎是红色的,可凉拌,可炒鸡蛋。可和面,擀成薄薄的饼,然后把调制的马蜂菜包起,弄成长蛇状,放锅里蒸,叫马蜂菜坨。
地里还有节节草、拉拉秧、葛八草、牛舌头棵、米蒿、灰灰菜、蒺藜。平原上,有多少人,就有多少草,这些草连一个响亮的名字都没有,都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字,虽然,人说苍耳就是曾在《诗经》出现的卷耳,我总感觉写的是另外的植物。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 ;嗟我怀人,置彼周行。”这是首怀人诗,多数人都解说是一个正在劳动中采卷耳的女子,想起了远方的丈夫,想到他在外会经历各种险阻,心中生出离思和忧伤。但有耕种稼穑经验,在乡土生活的人,都知道苍耳全株都是带毒的,是不可以食用的。也许,这个女子是中了思念的毒,喜欢这带毒的植物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但平原深处的人,喊不出苍耳这样文雅的名字,人们都叫它蔷子棵,我以为应该是戗子棵,蔷子,太温柔,女性化,不合乎苍耳浑身带刺的外貌,而戗子,才能还原苍耳的神与貌。我们这里的人把吵架,称为戗起来了,我有次读《儒林外史》,读到“两个说戗了,揪着领子,一顿乱打”,就像看到我的街坊进了吴敬梓的笔下,传神写照,以气图貌。我们把喝水时,喝到气管里,就叫戗(呛)水戗(呛)着了,词典里有解释:倒着长的东西,逆着的东西,不顺的东西,就是戗。
苍耳的刺是扎人的,粘人的,总感觉要是握着苍耳念《诗经》是一种滑稽。
在乡下,我见过姐姐的头发上,衣服上,总是粘着苍耳,姐姐要我帮她把头发上的苍耳揪掉,揪的时候会把姐姐的头发扯下几根,把头皮揪起,姐姐就疼的叫“轻点”,这才是生活的坚硬,和《诗经》里的卷耳简直是南辕北辙,有云泥之别。
二
要承认,苍耳,或者戗子棵是草家族的异类,在草的版图上,它不是主角,而我们鲁西南平原呢,在山东的版图上,是缩在黄河的身子下,是偏远之地,这里充满的都是草野之气,也不是主角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你说泥土气息也好,那里有黄土的湿黏稠的淤泥和干净如绵的沙土混合的腥味。一个村庄连着一个村庄,那路就是连起的针脚,没有太大的差异,只是这一片土,适合种花生,那片地适合种玉米,有的碱了,有的酸了,这是泥土的质地,与人一样,黑脸红脸。但我常常觉得天是灰蒙蒙的,这么一马平川的平原,却往往使人的眼睛疲倦,天是灰的,庄稼是灰的,特别是那春天,虽然有阳光,但大地上会弥漫着播种时晒大粪的那种刺鼻的味道。夏天,那些坑塘是沤麻的死亡的气息。
我是在这里长大的,我是这里的一株植物,是能走路的植物,虽然后来到了城里,但还是一株移居城里的植物而已,我一直有着可怕的自卑及自尊混合的那种内心的脆弱。城里人的那种先天的气质,我没有。
人们好像一提故乡都会莫名的激动,其实很多人,是故乡的累赘,或者故乡是你的累赘,这是一个被过度的渲染和思念的包浆遮蔽了原色的词,这里面多的是沧桑,这是口古井,曾经的你,是井中男孩,你趴在井沿上,那时井中的你,是怒马少年,有明媚的笑靥,有青春的肢体,但你也感到了沉重,这一片天地里,即使盛满一井的月亮,那能有几吨的月光呢?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也不能说乡间庸碌,但大部分人在生儿育女中循环,最后还是消磨了斗志,沉在了麻木里。当我20岁骑着自行车奔驰,从乡下到小城读大学的时候,开始的兴奋,被所谓大学的气味所击倒。这个学校就在郊区,是被几个种菜的村子包围在遗留下的护城堤外的一所学校,学校近旁的庄子,就是刘庄,菜刘庄,也有叫刘小鬼庄。
学校外面,就是大粪场,我的心一下子痉挛起来,原本想的大学,是杏坛白云,星空蓝天,西府海棠,紫藤长廊。但学校的院墙,满是洞,刘庄的人进进出出,如走进自家的堂屋门。在寝室里,我的泪流下来,挣扎一番,我还没有离开故乡,离开泥土,只是挣扎到一个故乡的边缘,一个被乡村包围的读书的地方。
于连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。我想到,他后来不是木匠。
1981年秋天,我的高中也没能走出我们村子,那高中就在家门口,叫鄄城三中。在那个秋天,我读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,罗玉君翻译的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,那个封面,是黑红两个色块,反白的书名,有几个男女,是舞会场面,是竖排的繁体字,当时读的眼疼,往往错行。
但谁的心里没埋藏一个于连呢?特别是那些底层的孩子,即使他白发苍苍,于连也会唤醒他。
我看到了于连,就如于连在心里给拿破仑留着位置,我在心目中为于连留下位置。在课堂上,读到于连用手抓住德瑞那夫人手的时候,我的两条腿打着颤,牙巴骨在交错,因为激动,我想在教室里喊出来,我像在茫茫的夜色下,挤压的河道中,在船只不知何往,也许要触礁沉没的时候,发现了爝火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“夫人,我出身低微,可是我绝不卑鄙。”这是我最喜欢的《红与黑》里的一句话,后来看到有人翻译为“我出身低微,夫人,但是我并不低贱”,这翻译更有力,更传神。
于连,才19岁的于连他绝不愿意为一个金币而向那些公卿大人们弯腰,他视阿谀奉承为奇耻大辱,他要凭自己的才干赢得人们向他脱帽致敬,也许卑贱的出身,使他对捍卫个人尊严更有过人的敏感。我曾神经质一样的敏感,特别是对那些白眼。当德瑞那市长准备聘于连做家庭教师时,于连的父亲老索黑尔关心的是报酬,为增加每一个法郎而准备拼命,但于连关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:和谁一起吃饭?“让我和奴仆一起吃饭,我宁可死掉。”当德瑞那夫人出于好心想送给他一笔买衣服的钱时,于连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。
“‘夫人,我出身低微,可是我绝不卑鄙。’于连站起说道。眼睛里射出愤怒电火花。他停滞了身子,傲慢已极。”(罗玉君译)
结果,德瑞那夫人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我懂得了,尊严是可以挣来的,那首先是自己的人格魅力,但应该所有的人格都受到尊重,不受到侮辱。别人都过好日子是别人打拼得来的,也许是运气,但应该是悲悯,不应该居高临下。其实在读《红与黑》的时候,在英语课上,老师讲到了美国民权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在1964年的梦想,1964,就是我出生的年份。有人出生,有人死去,有人心怀梦想,有人绝望而死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我向往着马丁·路德·金所说的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。向往着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。向往着我们现在并不满足,我们将来也并不满足,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,汹涌澎湃,滚滚而来。
我想,这也是于连所向往的。马丁·路德·金说:我有一个梦想,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,讲出这个真理——我们相信人类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,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。
这话,也是于连心里有,而没说出的。但吸引我的是于连的一连串的举止,在于连被聘为家庭教师后,第一天到市长家的大门前,竟然不敢举手去按门铃。其实,这也是存在于我身上的,当到一个陌生人家去,我总是胆怯,当母亲让我去见一个生人的时候,我总是脸红,好像是被捆绑起来的猪去屠宰一样。但当于连发现不敢按门铃的胆怯样子被德瑞那夫人发现时,就激起了于连对自己的憎恨,“……停留在府第的门外,不敢伸手按门铃,于连以为这是他的莫大耻辱。”正是这种对出身的自卑心理,他一直以为德瑞那夫人是看不起他的。这种虚幻的被蔑视感,激起了真实的自尊反抗。一次在花园里谈话时,于连无意中碰到了德瑞那夫人的胳膊,德瑞那夫人立即把胳膊缩回去了。这个动作,也许完全出于一个贵妇人的教养。想不到,又触动了于连的自卑心理,“变成他自卑情感的创伤”,以至于下决心要报复:一定要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我曾拿着《红与黑》把于连如何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的段落,作为秘密似的,让很多男生看。
“有一个晚上,于连说话很起劲——他讲得得意挥动起手臂来,因此撞着德瑞那夫人的手了,这只手倚靠在一张椅子的背上,油漆木椅是早就安置好在花园里的。
“她的手很快地就缩回去了吧。于连心想,这只手假如他偶尔撞着仍不缩退,这,他应该把它紧紧地握住,这是他的‘责任’。他这种责任的观念,使他想到假如她的手不再回到原处了,这就变成可笑的事,或者变成他自卑的情感的创伤。
“他无心教孩子们的功课,很快就结束了,不久,当德瑞那夫人来到眼前,他不禁想到胜利的光荣。他暗中决定,决定在今天晚上,要她把手送到他的手里。他要握住它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“终于大家坐下来了,德瑞那夫人坐在于连旁边,德薇夫人又坐在她的女友的身旁。于连一心一意要去实践他的企图,找不出半句话来说。
“他们的谈话没有劲儿了。
“于连暗自想:‘有一天我将和一个人第一次决斗,难道我也是这样的怯懦战栗和不幸吗?’他太怀疑了,他对自己与别人都失去了信心,这样他如何能窥见他心灵的状况呢?
“府第里的闹钟,刚才响了九点三刻,他还不敢有所动作,于连对于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,他暗自想等十点钟来到后再说吧,这个千金难买的时光,绝对不能把它放过。我定要履行我的计划。我整日所憧憬着的,所追求的,一定要在今晚上实现;否则宁可回到我自己的寝室里,打出自己的脑浆来。
“在等待与焦急里,于连的过分紧张的激情,使他几乎失去知觉。终于传来了十点钟的钟声,飘过他的头上,这命运的钟声每敲一下,在于连的心头引起一阵回响,他的肉体也不由得不跳动一下。
“后来,十点钟最后的一下了,在他的心里起着更大的回声的时候,他伸出他的手去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握着。但是她的手立刻就缩回去了。于连不知道怎样做才好,本能地又把她的手抓着。他在无限的感动里,他还感觉到他握着的手,冷的像冰霜一样,这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打击,他拼命地把这只手紧紧地捏着。她再努力缩回这只手,但是结果这只手还是在于连手中握着。”(罗玉君译)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当我在课堂上读到这段的时候,就像初尝禁果,一阵激动,下面一紧,接着很舒畅,自己也控制不住——当时很窘迫,等放学大家都离开位子,我才尴尬地站起来,跑出了教室。
司汤达于一八〇五年一月十四日写下过这样的日记,当时他22岁:“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。我强烈地盼望这两种东西,而且配得上它们。”
是的,于连卑微,但他有实践的勇气、征服的勇气、占有的勇气,他为自己的梦而拼杀,最后死去。我想把于连作为自己的偶像,那只是偷偷地,我不敢那样张扬。人们会嘲笑我的狂妄,不自量力,我胆怯,瘦弱,卑下,在一个平原的深处,就是一颗内心长着刺的苍耳,但表面应该是平顺的甚至是光滑的。
但我内心中一直供奉着于连的精神的骸骨,我们的梦想,都孵化于卑微的底层,黑暗的乡下,他的父亲是木匠,而我的父亲只是一个街头卖饭的小手艺人。我有着底层人的最彻骨的体验,其实这不是来自皮囊的痛,更多的是心灵的痛,那才是底层残酷的真。
我无法给任何一个人说,于连的梦想,就是我的梦想,但他确实是一个乡下孩子的梦想。我17岁时读到了《红与黑》,知道了于连,在我写这文字时,我在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到了那个版本,就是还原我当初读到于连的惊悸与感动,这是我曾经梦到的情景,我今天的血液里,还泛着挣扎的光焰,我能感受得到于连的存在,甚至我能和他对话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但我说于连是法兰西的苍耳,附着在城堡的石缝间,艰难生长,最后陨落。
三
我一直认为《诗经》里的卷耳不是苍耳,它和爱情无关,它就是《本草纲目》中的一味药,苦、辛、微寒,有小毒。主治:久疟不愈、眼目昏暗等。
也许,我就是带毒的,是小剂量的毒,不是那种杀人越货、在刀尖讨生活,敢以血计酬的主。现在尘埃落定,能静观自己人生的时候,我一直回避农村之子的身份,有时是更突显。即使我在城市安顿多年之后。
它曾是我的耻辱,摆脱乡村,摆脱灰暗的乡村生活,好像在乡间生活,是那么的卑微,我的祖辈一代一代生存在乡野,他们也曾有苍耳之愿,可惜是苦命,这些苍耳没有远方,还是在脚下的土地挣扎。
当我在乡间高中读书的时候,一篇习作在省里获奖了,被邀请到省里领奖,当时全省获奖的只有五六个人,一个乡村的孩子,见到了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作者,也见到了大书法家魏启后先生,只觉得当时魏先生在我的本子里写的字,歪歪扭扭,等理解魏先生书法的时候,那个给我留言的本子早就不知丢到哪里了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我从济南领奖回来,感到周围起了变化。在那个逢集的半夜,父亲要起来到集市上打扫卫生,而他的伙计,比父亲还大两岁的,按街坊辈分我喊二哥的马新胜,就对父亲和母亲说,木镇棉花加工厂的厂长家,要他来提亲,把厂长的独生女许配给我。那时,父母亲在堂屋的西间,我在堂屋的东间,中间是所谓的客厅,三间屋子,用高粱秸秆做成的箔隔开,但声音传达到了我的枕边。
厂长家的独生女与我同班,位子正在我的后边。
母亲很兴奋,一个农民家庭能攀上一个吃商品粮的家庭,那得是多大的造化?
我知道,我如果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他们家是万万不会将女儿下嫁与我的,所谓的穷小子和公主,那只能是在童话里,如果于连不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进入市长家做家庭教师,他是没有机会握住德瑞那夫人之手的。
那是我渴望成功,也是欲求最强烈的十八岁的年纪,但男男女女的情史也搅动着我的心,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沟坎,或者是陷阱,或者是困境。我在初中就偷看《生理卫生手册》,主要是看里面的生理卫生和彩色图画,对人体的生理结构,充满好奇,看到女生的身体,躯干、乳房、生殖器官,都莫名的激动和亢奋。
每次看都会引起生理反应,我知道女人也是男人幸福的构成,也是男人最原始的动力和源泉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那出身的自卑,是横亘在我面前的鸿沟,我和厂长独生女的差距,只是一个购粮本,她是天生就有的,我必须奋斗才能获得那个小小的购粮本。
厂长的独生女名叫黎明,每次到上课的时候,才到教室,有时在教室外喊报告,老师说进来,才扭捏进来。黎明当时婴儿肥,微胖的身体在我背后坐下时,能感到她的呼吸。其实她家离学校很近,只隔一条路。在我因为获奖被县城的一中要走的时候,我在一中收到了黎明的信。彼此都是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,我知道这不是恋爱的时候。她家之所以到我家提亲,是赌我未来有出息,没有未来,一切还会回到原点,我依然在农村,重复着父亲的命运。而她会和别人拥有爱情和家庭。
在一中的一年,我钻在被窝里,也曾幻想,是该从我开始改变农民后代的基因的时候了。原本在预考全文科班第三的成绩,却在高考时,被数学拉了后腿,120分的数学我只考了50分,虽然我的历史地理都是全县第一,而语文也是前列。
我只能到一个专科学校去了,大家都劝我复读,但我确实怕了高三复习的紧张,一个班里,晚睡的和早起的在教室会合,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,快一米八的个头,只有90斤,走路都觉得发飘。
即使高考过去多年,做噩梦却仍是高考,总是到交卷的时候,才发现还有一张试卷没有做,这时就急得哭着醒来,几十年这场景从未改变。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
……
(节选于《安徽文学》2022年第1期“散文精粹”头条)
傲世皇朝:www.jhc10086.or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