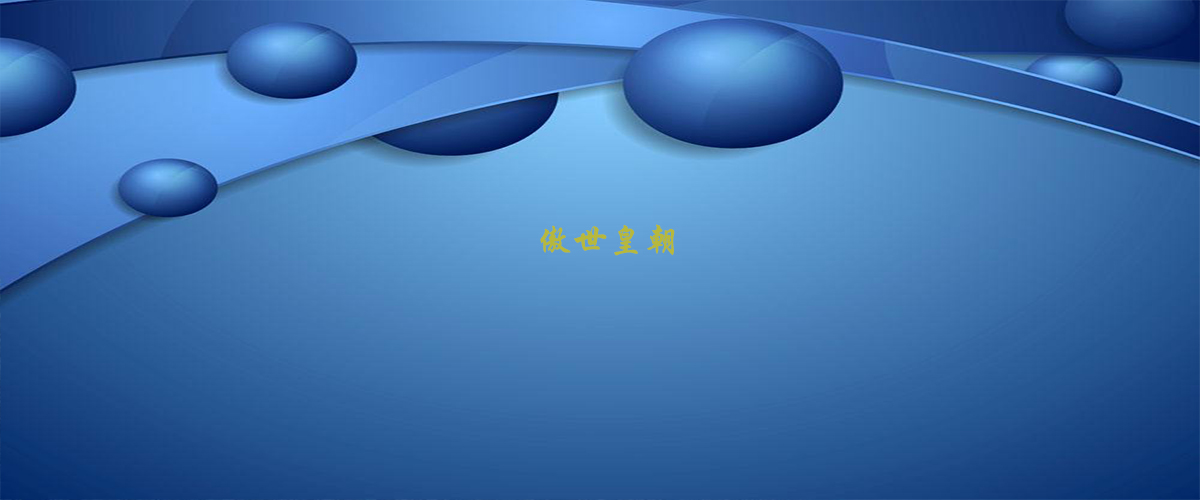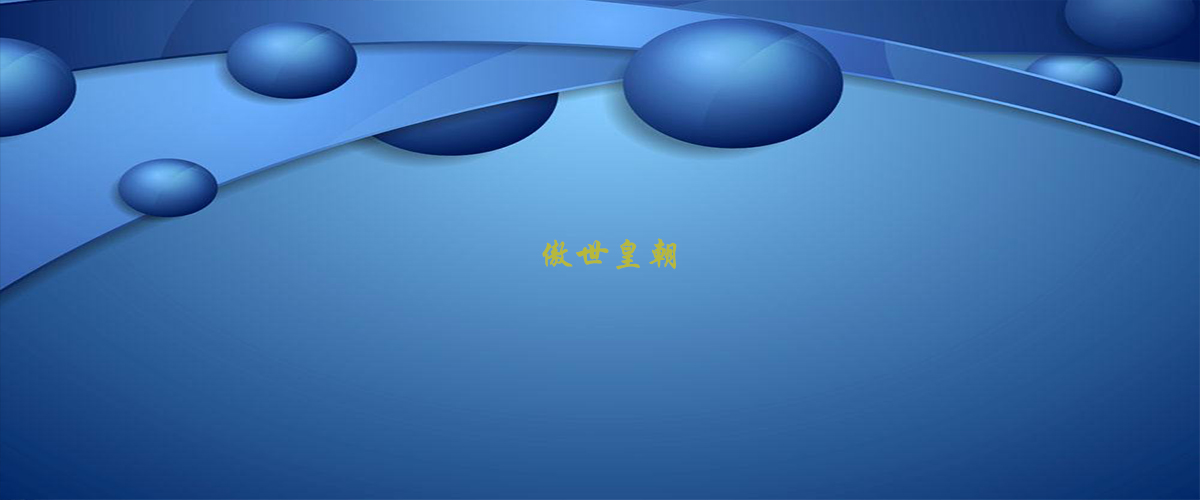傲世皇朝平台|《青年文学》2021年第11期|袁远:成都,成都
傲世皇朝快讯:
袁远: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等刊。出版有小说集《一墙之隔》《单身汉董进步》《纯属巧合》,长篇小说《亲仇》。曾获第六届、第九届四川文学奖。现居成都。
成都,成都
文/袁远
一
多年前,成都是我的异乡。住久了,往事长进记忆,流光生出根须,缓缓撑开记忆地图上的山川草木,城廓街巷,于是,异乡渐成故乡。
我第一次进成都,三岁那年。父母带着我从北京南迁贵州,目的地黔东南,一个藏于深山的保密基地。途经成都,短暂停留,我的手因而拽住了成都猛追湾老游泳池池边的一根铁栏杆。这动作保留在一张黑白老照片上。梳童花头、穿灯芯绒外套的我,站在成都初冬阴云低垂的天幕下,面带迷茫一笑不笑,似对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,感到疑惧。
再来成都,火车穿越白昼与黑夜,大小行李肩背手提,一头走进大学校门。四年光阴,除了校园,最熟悉的莫过于校门外人头攒动的老培根路,夜间昏灯下摆摊卖旧书的老九眼桥,女生们拉手挽臂去淘便宜衣服的老春熙路,还有就是当年的空军礼堂了。坐在男生自行车后座上,薄雾染白的夜色轻微鼓荡,凉风推着雾气刷过耳畔,而激昂的诗歌朗诵会,小众的文艺电影,喧嚣的川剧表演以及魅异的实验话剧,正在夜的那一头,张开怀抱。傲世皇朝注册
毕业后离开成都,再来已是两年之后。辞了公职、丢了铁饭碗的我,再不是当初有校园可寄身的学生了。若把成都比作文学世界里的巴黎,那时来自一个二线城市的我,无疑成了巴尔扎克笔下,一穷二白的“外省青年”中的一个。
有人说,每个走进大城市的人,皆有自己所求,或求生存,或追梦想。我去职来到成都的初衷,是找寻朋友。不是找某一个,而是找某一群。在我想象里,那是一个把文学当空气来呼吸的异质之群,是把日子过得飞起来的一个别样族群,是现实生活的叛军,是令人瞠目的异端。他们与我相不相识无关紧要,要紧的是,当我抬起眼,能望见那群人飞翔的身影,能听到他们飞翔的声音,能感受到空气中的闪电与震荡,那就足够美妙。
现在回头来看,倒不是这想法过于文学青年而让人发笑。有意思的在于,我其实是个特别不善于跟人交际的人,给人打个电话都有各种心理障碍,在人群面前,永葆退缩之姿。于是,我这个前来找寻想象中同类的人,一路退缩着,默默旁观着,终于随着时光之河的淙淙流淌,如期退到一个僻静角落。当然,这个角落,是成都提供给我的。
二
不管怎么说,来到陌生城市,生存总归是第一要务。我在成都念了四年大学,但对于当年的我,这座城市仍是陌生之城,东南西北都辨不清。托成都是“媒体之城”的福——此地报纸最风光的黄金时期,为上世纪九十年代,大小报社比比皆是——我到成都第二天,就在一家报社谋到了工作。其后这些年,多数年头我吃着报社编辑的饭,也做过杂志,基本没脱离这个行当。傲世皇朝注册
数年前我在一篇随笔里写过一句:“成都给人的一个幻觉是,在这里,过好日子根本无需勤劳勇敢,好吃懒做就行了。”有此幻觉,并非空穴来风。成都天生有种闲散气质,人们走路总那么慢吞吞,餐馆随时坐着吃喝的吃客,茶馆里整天粘着打麻将和斗地主的闲人。真的啊,没有哪一个城市像成都这般坦然自如、无怨无悔地追求吃喝,并在形式上充分体现出来:这城市几乎全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进食状态,每一条街上都能找到饭店、面馆、小吃店,每一条街都可谓餐饮一条街。而且茶馆也卖饭,饭馆也卖茶。当年如此,至今依然。
但事实上,好吃懒做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待遇,确乎幻觉,尤其对“外省青年”而言。回到我在成都谋生的初期,小报社里谋职收入低微,只能租住城郊简陋结合部的民居,冬冷夏热,老鼠成群,开水瓶里水垢厚积。那几年,跟我一样从外地来到成都并在报界打拼的一众青年,多是低收入。说起来,我们是编辑、记者,其实,食不果腹的日子也有。这么说,不是夸张,更非卖惨。某年某月,我供职的一个小报社遇风波关停,下一份工作一时间找不到,我和一同龄女同事,头脑发热决定做自由撰稿人。这个冒失的决定,很快把我俩带入囊中空空的境地。弹尽粮绝之前,我们花掉了仅余二十多元中的二十元钱,路上还跟来了一条待价而沽的小奶狗,我们用余钱买下一盒牛奶一块面包做狗粮。小奶狗拒绝进食,它被我们带回来后就生病,狗与人,病的病,饿的饿。奇怪的是,日后我的大脑记忆库中,却难觅饥饿记忆。或许因为年轻不记困苦的经历,也可能还饿得不够狠。可见,人的记忆会拐弯,也可以说,记忆是一张网,留下什么漏掉什么,它自有主张。傲世皇朝注册
在另一家小报社,办公场地是租来的老房子,日光灯照不亮昏暗办公室。编辑部有三个编辑,共编四个版面,还得自己画版,其时还是纸质办公条件,画版全靠手工。校对也是我们几个编辑的活儿,此外,还要轮流到印刷厂值班。这且没完,报纸印出后,我们得帮着人手不足的发行人员,清早就赶到报刊发行一条街,吆喝着把报纸批发给零售小报贩。身兼数职,薪水却挺不起腰杆,不敢问津街边卤菜摊上最便宜的猪肝、兔脑壳。不过当时的我们,对钱多钱少并不十分关切,记忆中,那是我在报界工作最惬意、最堪留恋的一段光阴。傲世皇朝注册
惬意和留恋,是因为编辑部里来来往往的人:诗人,准诗人,一腔激情热爱着文学或新闻的年轻人。诗人A,烟支夹于拇指与中指间,发乌嘴皮咬住深吸,每出一截烟灰,食指轻抹,抹出殷红烟头。文学青年B,言辞慷慨,好谈也好战,舌战到我们收工下班,一拨人,总是四五个,齐拥到街头小餐馆,吩咐老板或老板娘,两瓶啤酒,一碟花生米,随便炒两只菜,总共不超过二十元。老板端来酒菜,附送免费泡菜与茶水,任由我们对着吃空的菜盘,就着杯续免费茶水,高谈阔论到深夜十一二点,他从不催促,也无怠慢,好像我们的邻家大伯、隔壁阿姨,好像我们不认识的远房亲戚,纵容着我们。
如果我没记错,大约每周,我们都会到小餐馆来一次这样的盛宴。当我们围坐油污餐桌,以各样外地口音,大张旗鼓谈论文学艺术、新闻奇闻和天下大事之时,别桌食客是否对我们侧目而视、翻白眼,我毫无印象。以成都具备的对各种怪人怪事强大消化能力的体质,我推测,我们并没遭受多少白眼。
这是我喜欢成都的原因之一。在广阔的民间,在腾腾烟火气之下,对外地人和本地人一视同仁的友爱与宽厚,铺陈于日常生活的河床,看得见摸得着。类似的事情多了,我与当时依然不熟悉的成都之间,彼此慢慢确认了眼神。傲世皇朝注册
三
生计问题总归会解决。
就我们这些“外省青年”来说,即便在貌似以游手好闲为己任的闲散成都,解决生计肯定不是靠整日喝茶。当然,不少生意和业务是在茶桌饭桌上谈成的,这是另一话题,暂且不谈。不过,成都这地方确有一批人,能够不动声色、无为而为地,把该做的事做了,把该挣的钱挣了,然后,就是喝茶打牌吃美食。成都的特点在于,无论事务多么繁忙、生活多么奔波的人,总不会耽误一杯闲茶。但凡遇着空中太阳出巡,就是理所当然的喝茶日,这是成都人的共识。
我后来应聘进入一家规模很大的报社,其发行量、影响力在本地是数一数二的。印象中,报社的外地人要占八九成。成都调子再慢,生活再闲,在这种大报社里的工作,情况就完成不一样了。我们的工作总在高速运转,记者手机二十四小时待命,半夜两三点被从床上叫起披挂上阵;编辑连轴熬夜熬成兔子眼;从早到晚催命似的电话铃声、催稿的叫喊声、上司的训斥声、下属的应辩声、敲键盘的噼啪声、如风一样来去的脚步声,交响不绝。我在报社副刊,相对不那么紧张,却也绝不轻松。我们做的是大副刊,部门因而配有记者。女记者Y,我们昵称小绵羊,五官纤细身段玲珑,干劲、冲劲、耐力不让须眉,赶稿至凌晨,天亮后又有新任务,家也不回,三把办公椅拼成简易床,和衣一躺,数小时后起身洗把脸,即刻精神抖擞。傲世皇朝注册
自来,四川女子骨子里有股泼辣劲,成都发达的传媒体系,激烈的报业竞争,又相当豪迈地为本地输送了大批“女汉子”。虽然我依旧不擅与人打交道,在人际交往方面总做不到游刃有余、进退自如,可是谈吐举止也大有了汉子之风。那时我们部门的几个女子,张口“老子”闭口“老子”,做事个个手脚麻利,闲谈说笑间任务一来,一个转身,迅速进入工作状态。
生计不成问题之后,是向上走,求升职?向前跨,求财富?转个弯,发展个人产业?还是散淡下来,爱做什么做什么?这就又面临选择。向上走、向前跨,自然不乏其人;发展个人产业,随后成功转型,案例亦不鲜见;然而,不求位不求钱,只图个逍遥安适、自由自在,这样的人,成都同样会成全他。多年以后,我见到当年一些老同事,无官位的、没发财的、连工作都没有的不少,却没什么人愁眉苦脸,该谈笑谈笑,该喝茶喝茶。本来嘛,沧海一声笑,纷纷世上潮,高高低低不都是日子,进进退退不尽是人生?
就是在那个报社工作期间,我开始像成都本地人和新本地人一样,时不时泡茶馆。大慈寺里的露天茶馆,是我们常去之处。古旧建筑,参天老树,青砖院坝,青花茶碗,成都经典的阴天伴着茶香氤氲。那些嘎吱作响的老竹椅,托起了多少人的浮生半日闲,或者,成都式的忙里偷闲。一把竹椅安坐,身边朋友三四,茶水穿肠一过,不说天清地明,也自有一份心平气和。傲世皇朝注册
四
当一个外乡人,在一座城市有了房、置了业,获得了安身之所,按通常标准,就等于安居下来了。到这个阶段,你基本会万无一失地发现,日常生活提供的可能性和戏剧性极其有限。两点一线,毕竟是大多数人的常态,城市再大景观再多,生活到底欠缺流动性。精神领域的通关,上升为紧迫之事。
我在成都这些年,有一段不短的时间,内心里总有一个死不改悔的声音:“离开,离开!”每过一时,这声音就要鼓噪起来。成都是安乐窝、温柔乡,然而生活的悖论恰恰是:生活在别处,风景在他方;成都情长故事多,而同时,这里又是一批生活梦想家注定要常怀惆怅之地。毕竟,城市的最初版本,就是合围,围起一片免受外地侵扰的区域,安放众人的温饱,守护人群的繁衍,可焉知,这又不是一种画地为牢。
离开的冲动不是我的个人专利。当年我随手写下过一批小随笔,那些随笔记录了那年月,三十岁上下、渴望离开成都远走高飞的人,俯拾皆是。他们好比溺水之人,急于浮出水面换一口气。都说,成都来了就不想走,其实多面的成都,具有远超这个简单论断的丰富性。有人来了不想走,有人来了却想走,有人走了又来,来了又走。这才是成都。而我,真的离开了,从成都出发,一去去到南半球,遥远的非洲,非洲的南端。曾有一些朋友问过我,为何要走得那么远。这又要说到成都了,早年的空军礼堂,在我读大学期间,放映过一部影片《走出非洲》,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非洲辽阔的异域风光,迥异的人文风情,如受电击,心醉神迷。那就是根源所在。傲世皇朝注册
在国外的日子,实话说,我没怎么想念过成都,然而每当别的中国留学生向我问起成都时,有趣的事情就来了:一开始,我总是想一分为二地介绍它,但每次说着说着,就变成了唱赞歌。我终于发现,在成都生活过的人,对这个城市总会有不那么容易戒除的精神成瘾性。
在国外生活近两年后,我又回到了成都。似如游子归乡,漫长归途中,我体会到了回归成都的急切心情。小时候,我随父母辗转迁徙多地,心中并无什么故乡概念,正是那一次的离开又返回,我确认了这个地方,我愿意回去也回得去的地方,我已然久居并还可以久居下去的地方,这,就是家乡。
五
在成都,我曾经住过的城郊结合部,如今早已华丽变身,成了热闹主城区的鲜亮部分。我后来住过的玉林小区,就是那首近年风行一时的歌曲《成都》唱到的地方,有诗人翟永明的老“白夜”,有“摇滚教母”唐蕾的小酒馆,这里是成都时尚生活与文化生活紧密拥抱的标志性地带。再往后,我搬至三环路边,继而搬到主城区外,离喧嚣热闹、离中心区域越来越远。作为一个从不长于“快进”向前的人,我享受到的成都版图不断扩容的福利,就是在城市的偏远处,找到了自己的安谧一角。傲世皇朝注册
这么说吧,有千万个住在城市的人,就有千万种城居生活。都城的广大浩瀚,足够雄心驰骋、野心膨胀,足够一腔壮志挥斥方遒,同样,也会不消停地生产孤独、惶惑、胆怯、失意、疼痛与唏嘘。前面说过,我的生活步姿是一路退却,那又何妨,这样的生活,也能捧起一杯茶,看晨昏交替,忆往事如风。
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:www.jhc10086.or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