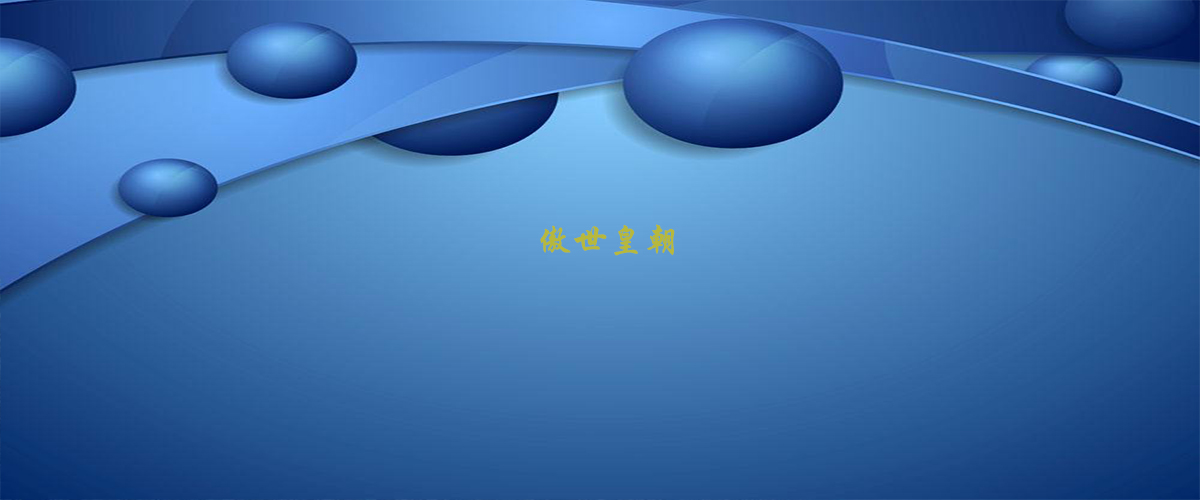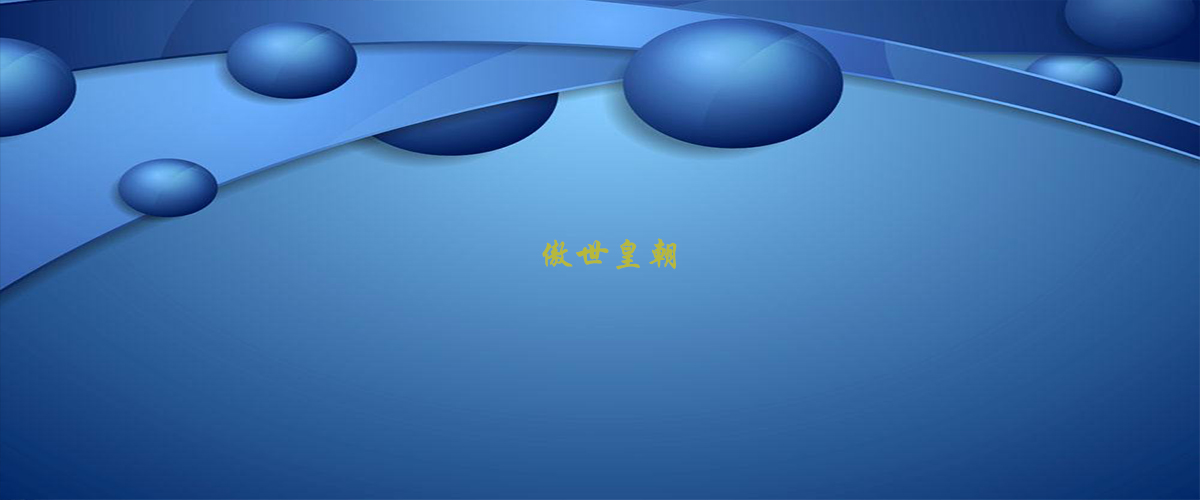傲世皇朝|《草原》2021年第9期|查娜:病过四季
傲世皇朝娱乐注册报道:
这是我已经过了四季,未来不知还要持续多久的顽疾。其实在此之前,这顽疾曾心慈手软犹豫许久,迟迟未射出那颗致命的子弹,并用持续一个半月的莫名咳嗽提醒我。伴着不可遏制的干咳和自认为解决问题的白开水,我在那些反复提示的有限时日里不以为然,又被千头万绪的事情牵扯着上蹿下跳甚至风驰电掣,全然不知它早已淡淡微笑,盘桓左右窥视我多日,并以全然的昏厥将我掀翻在地。
冬末的手术室
那是个永远都横亘在我心间的冬天。其实冬日已经所剩无几,在被摔得全身青紫之后,寒冷又被无限延长。
印象里是穿越了无数的检查和医院里永远的人海,依然干咳着并且左下肢肿痛异常的我被告知,情况危重需要马上手术。
躺在病床上被从病房移动到手术室,记忆里还是第一次。屋顶上的白色迅速掠过,然而那白色又绵延无尽,长路漫漫,伴着凛然干硬的寒冷。盖着巨大的被子,我依然觉得耳畔风声呼啸。护士的脚步匆忙坚定,我的心,突然随着病床的快速移动剧烈地跳了起来。我充满确定性的生活和那一条又一条的计划,就这么被彻底打乱。
会是什么样的医生帮我手术?在病房外,我心里居然还能盛满好奇。依旧是冷,我裹紧了被子,睡意莫名袭来。似乎有人在观察我,我缓缓睁开眼睛,看到一双温和善意的眼睛,医生接手了我,我被推着又进了消毒更为严格的介入手术室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好几个助理医生围上来,帮着术前准备,许是因为看到我慌乱,他们热情地和我聊着天,平日并不多言的我因为紧张在喋喋不休,说我正在写的书稿,说我忙碌中的大意,说我数次昏厥而不以为然的愚蠢,略带夸张甚至没有停顿。一时间,我听得自己有些尖厉的声音频率极高地四处乱窜而且无法控制,手术台居然是一片忙碌而热闹的景象。
左脚要输液,一位女医生把那只脚的袜子轻柔地褪下来,麻利地给我穿到另一只脚上;口罩当时极为稀缺,我还戴着的口罩,主刀的医生帮我拿下来,对折好装进病号服的衣兜里。暖意,让沿着眼角流下的泪水不那么冰凉。
那泪水里,还有控制不了的恐惧在摇摇欲坠。几乎是突然之间,我一个人躺在巨大的操作台上,两个大屏同时移动起来,身体在被透视,恐惧从心底升起时不可遏制,它如此强劲,瞬间击垮了我,裸露在外肿胀烧灼的病腿忽然变得冰冷,我的手找不到可以放置的地方,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寒意将我全然覆盖。
我像是放置在高处的祭品。所有恓惶推动着未曾考虑的问题突然奔涌过来,几乎成为巨浪,最大的一个浪头是,我不会死了吧?如果有这样的意外,我这么多年左省右省一点一点给11岁女儿和年迈双亲攒下来的那些私房钱可怎么办?它们存在我那些自己也分不清的银行卡中的一张上,又有谁能挑出来?又告诉他们唯有我知道的密码?而死后,又会如何?我昏迷前在镜中看到的那些漆黑和暗黄是死亡的颜色吗?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从来遥远的死生和我关联得那么突然。它们呼啸而至,可我毫无准备。恐惧,被无力阻挡的寒冷,无从安置的牵挂,无法把握的未知和刹那觉知的遗憾堆砌得结结实实,横亘在我心头,心脏无从负载这沉重,它被加速压迫时又如此迅猛,只是瞬间,心率就飙升到130。
我听见医生们在议论我的心率,在遥不可及的地方。孤独前所未有,排山倒海袭来。我是一个人。我得鼓起勇气,协助医生让那些可能要进入我身体的各种器械顺利到位。此时此地此间,只有此身能度。我努力摸索到手的位置,还没来得及抓住什么,医生让我放松,病腿的一处被当机立断切开,手术开始了。
我在一条狭路上行走,前路茫然,踉踉跄跄。意识只够听得耳畔各种器械的声音,医生的询问遥远而笃定,清晰又模糊,身躯和意识原来都如此滞重。手术的结束是我被绷带紧紧绑上,全然不动的姿态,为那些可见不可见的伤口争取合上的12个小时。
我还活着。在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瞬间,我只来得及转头,看了看那个不知道盛放过多少病人生死悲喜的手术台,此刻它空空如也,大多数人从它上面活着下来,也有一些,永远离去。向生挣扎的那些百转千回和惊心动魄,于死者将永远封存,于生者会结痂或是忘却。死生之间,终究只是一段一个人的孤独旅程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早春的母亲
困居病榻还是第一次。住院的消息没有告诉远在江南的父母。新冠疫情仍然蔓延,我们南北千里相隔,思忖再三,北地早春苦寒,没有必要将他们从南方的温润和梅花盛放中拖拽出来。
可是,母亲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情。她的心疑其实没有道理,而我只能如实相告,自己生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病,现在是术后,就快出院。
疫情肆虐之中流动会被限制,长时间机舱内的出行被认为风险极大,七十岁的母亲还是高危人群,以及回来可能被隔离,电话里我们都很理智,约定一南一北,暂不相见。
然而正是我出院那天,母亲回来。
远远的,母亲站在我的家门口。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,什么都没问,只是和我笑着说一路安检诸多,见了的人几乎都穿着防护服。许是为让女儿和我放心,她反复强调,她应该是安全的,因为一路上戴着面罩、口罩,也戴着橡胶手套,没吃没喝,就为了不给病菌可乘之机。从南北归,是七个小时的旅途。把自己用橡胶塑料制品裹得严严实实的母亲,四个小时颠簸在车里,三个小时起落在飞机上,而晕车腿疼,是她的老毛病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也是远远的,我小心地扶着墙看着母亲细致地给自己消杀。雾状的酒精在她稀疏花白的头发上停留得那么久,我笑,妈妈要把头发也喷掉了,母亲也笑,不怕,头发掉就掉了,瘟疫可不能跟着我进咱们家里。酒精又迅速到了身上,极细的雾珠笼罩着母亲,那些雾珠迅速从她驼着的背上滑落,因为,妈妈的肩膀也是耷拉着。
本是春来,万物正要蓬勃,我第一次发现,母亲变得瘦小了。一米七○老是挺胸抬头的母亲现在低眉顺目,当她屏气凝神将鞋底也彻底消毒时,我看到她在归顺一个巨大的不可知力量。
变了的还有母亲的脾气。雷厉风行的母亲突然柔和下来,她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轻言细语。她从来都不问这个奇怪而麻烦的病啥时候好,只是紧紧地盯着我的药盒,每一颗药都不会落下,而每一次吃药时,都要目光炯炯地递过水来,然后直直地盯着我仰头吃下药去,一次再一次,认真而努力。
母亲回来后的饭桌也变了。很多年并不特别关注菜蔬饭食的母亲,开始戴着眼镜严肃地研究食谱,那些从电视上、广播及时记下来的食物烹调方法被大量写在卡片上,放在家里各处。我常常捡起那些随处可见的卡片中的一个,笑,怎么写了那么多错别字,妈妈还大学毕业呢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错别字连篇的食谱笔记,让饭桌变得五颜六色南北汇聚,厨房里整日都热气腾腾,各种料理器具往往是在同时开动,那些轰鸣我即便路过也听得刺耳,母亲穿梭其间浑然不觉,她像是在面对我的病魔时生出了和它作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,一顿又一顿的饭,是她的武器。清亮的稀粥,细软的肉糜,奇奇怪怪的豆子汤,五颜六色的水果汁,蔬菜绿肥红瘦,它们和我的药一起,前所未有地在我的身体里浩浩荡荡行进,成了我身上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力气。
有了只是一点力气,就老想出门看看。塞北四月,迎春花已经开上枝头,而我眼巴巴地看着窗外,已经几十个时日。
被软磨硬泡了好多天,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,母亲带我出门。你走在我后边!母亲提高声音对我说,像是走在她身后,春寒和微风都能减弱些,又像是,我们的前面,不是盼望了许久的春天,而是一个怪物可能伺机扑来。
我走在母亲身后,亦步亦趋。只是月余,新生的白发就让她头顶成为苍茫的暮雪。母亲抬着头警觉地走在我前面,不时回头叮嘱,慢点,一定慢点。其实很多年里,母亲和她的叮嘱一直在我前面,只是我自己不曾觉察。
秋天的父亲
一次又一次的术后复查,都是父亲陪着的。往昔拎着公文包的他现在站在我身边时,背着的是一个军绿色的粗布斜挎包。包里,是一个我喜欢的大号粉色卡通保温水杯,还有我每次做完检查都会拿到的一摞检查单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本来是智能手机盲的父亲突然学会了检索与我病情有关的各种资料,下载、转发给我后,总会再三确认,我发的资料,你看了吗?看到电视里有相关的医学知识,父亲最忙,除了拍视频,还会记笔记、画要点,然后电子资料、纸质资料都标上日期,一并交给我。
我的病应该多饮水就是父亲从大量信息中捕捉到的。时常,进门第一杯是水;出门约莫将近半个小时了,父亲就会从他斜挎的包里取出水杯递过来,即便不想喝,温和的父亲也会不容置疑地说,喝一口,就一口。我便喝上一口,是恰好入口的温度。
在医院,等待检查的时间往往会超过检查本身的时间。心情比医院的气味还要复杂,我们两个总是在医院的长椅上不言不语地埋头并排坐着。父亲紧盯着大屏,等待我的名字出现,好像我不识字。父亲常问的一句话是,口罩戴好了吗?我便紧一紧口罩。在医院,父亲如临大敌,眉头不自觉地皱着,好像路过的每个人都可能给我传染上什么疾病。几次检查过后,父亲就熟悉了流程,他会准确地掐好时间节点,尽量减少我在医院的盘桓,他和老妈一样,把我当成了玻璃娃娃。
那天上午,逾时既久,我突然听见父亲在对着分诊的护士大发雷霆,因为我的预约单被弄丢了。暴怒的父亲,我看到他的手甚至头都在颤抖,所有皱纹都挤在一处成为沟壑,声音异常洪亮地在和那个漫不经心的小姑娘核对。父亲本是书生,那一刻的高声和那个在父亲手臂的挥动中被甩在身后的巨大斜挎包,让他直如一介武夫。我拉着父亲坐回座位上,父亲沉默着调整呼吸,我努力不让眼泪落下来。那个难缠的病,放大了这个完全可以忽略的错误,生生把父亲逼到斯文扫地之境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无论在职还是退休,父亲日日与字纸相对,敬惜字纸是他的意识也是习惯。在对待检查结果的那张纸时,这种敬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医院拿到检查单后,不管结果好还是不好,他总是把每一次的每一张检查结果单都平整好,次序井然地用一个小夹子夹好,再装进透明文件袋里,最后才放到自己的挎包。回家后,第一件事就是摊开这些检查结果单细致耐心地比较,这一次和上一次的指数比较,这一次和第一次的结果比较。冬春的很多次检查过去,父亲齐齐整整地攒着我的检查单,我们全家人心里的明亮和黯淡,都写在上面。
那天的检查遭逢前所未有的秋风,无边落木萧萧下,踩上去声音刺耳,秋叶不断飘零,一切都纷乱起来。我和父亲各自裹着秋季最初的寒凉进了医院,惊讶地发现似乎所有的病患都被这秋风驱赶到了医院。人满为患到接踵摩肩的程度,秋季带来的干燥让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耐烦,等待检查的时间也在令人绝望地无限拉长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我在人声鼎沸的杂乱不安中站起来活动病腿,想着走得远些,离开这纷乱,哪怕,只是暂时。要打个招呼时,才看到被扰攘包围的父亲睡着了,在医院冰冷的不锈钢椅子上。第一次,我像一个陌生人,隔着人山人海凝望爸爸。
在睡梦中,父亲也护着他那绿色的粗布挎包,这时,它在他的胸前,被紧紧抱着。不像其他陪着病患来医院的年轻人,他们入睡时四仰八叉,充满与整个世界作战的勇气甚至耐力,此时的父亲蜷缩着,头垂在胸前,挎包在怀里,那小心翼翼的样子,像是要绕过一切可能的侵袭,护佑住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在生命的秋日里,背着斜挎包的父亲还在为我暗暗吃苦。那些担惊受怕奔波劳累之苦,逼着年迈的父亲换了姿态,拿公文包的轩昂,变成了斜挎着包求得安全方便的防守。这看去退缩着的闭藏秋意深浓,只是为了能积攒力气,带我山海泥淖越过。
夏天的痛哭
像是受降水的影响,在夏天,更容易雨泪滂沱。住院的几次,我都像个面对病魔的战士,咬紧牙关让情绪成为绷紧的钢丝,铁板一块就没有失控的时候。是在出院后,我的内心变得雨骤风狂。
第一次痛哭是在小满,因为鞋子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我从来没有想到,有一天,因为无法全部消退的脚肿,我那些秀气狭长的高跟鞋、猫跟鞋,会全都穿不进去。门外是花红柳绿在娇妍明媚,已经换好了长到脚踝的法式连衣裙想要融入那初夏的晴热,满心的欢喜就要跳出胸膛,站在满满一柜子鞋之前,没有一双鞋子能装下已经不一样的双脚。突然想起还未发病之前,曾经想跑个半马,好像是专门买过好多双非常专业的半马鞋,有一双居然刚好能穿进去!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,然而,穿着拖地长裙搭配着半马跑鞋,又怎么出门?而那即便是最好的跑鞋,也已经再没有用武之地。这些,会不会就是此生?那正来的此生,让我泪如雨下,也终于让我穿着跑鞋长裙行走在阳光下,此后屡次。
芒种的到来让疫情短暂消散,女儿的网球课也开始恢复,我终于能有送她去上网球课的力气。那是病后,我第一次进到自己曾欢快挥拍奔跑的网球馆里,绿色的地面和白色的球网没有任何改变,甚至因疫情相隔许久的孩子们和教练们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站在场边,我仔细端详打网球的女儿,她开始在场地上姿态优雅地发球,判断稳准地接球,畅快而富有操控力地奔跑。教练过来问,姐,今儿有空吗?你们娘俩拉练一下?教练知道,和女儿拉练,把她调动得满场奔跑是我的拿手好戏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不打了,我还有事。我笑着和教练说,用病腿能承受的最快速度转身扭头向门口走去。我几乎一刻也不想站在我和女儿共同的启蒙教练面前,解释我说的有事。同样的惊恐再次袭来,是不是我的网球之旅也就此戛然而止?比我走路的速度还要快得多,眼泪夺眶而出,翻滚而下,那是无奈也勇毅的告别。
夏至。四个发小隔着一个生离死别的新冠疫情,在手机上商量继续我们一年一会的相见,这一次是在海边,厦门。电话里的大呼小叫,是我们在安排着可能到来的一切。兴高采烈地订好机票,看到几乎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,猛然想到我的腿,无法承受超过一个小时的空中飞行。眼泪,一滴又一滴地安静掉在我的手上,我该怎么告诉发小,交通已然便利到咫尺天涯,我却无法奔去?而遥远会远到遥不可及,这可能,也是我必须接受的此生?
在一年当中最为灿烂的日子里,这些正在路上的沉重此生,生生在我心上划出一道又一道血肉模糊的印痕,因为,这个病也许下一个季节就好,也许,它永远不好。而我,只能以接受为药,让它们很快结痂,那些夏天的泪水,带走了哀怨,而我终将在四季的轮回中坦然,病苦本是生命的盲盒,在那些由它打开的未知生命航道上,我所能为,只是一路与它同行,又如它般淡定浩荡。傲世皇朝平台注册
【查娜,本名崔荣,文学博士,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中组部第十四批“西部之光”访问学者,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,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批“草原英才”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中国青年》《散文》《草原》等刊物发表散文多篇。】
傲世皇朝娱乐登录:www.jhc10086.org
下一篇:傲世皇朝平台登录|番号的味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