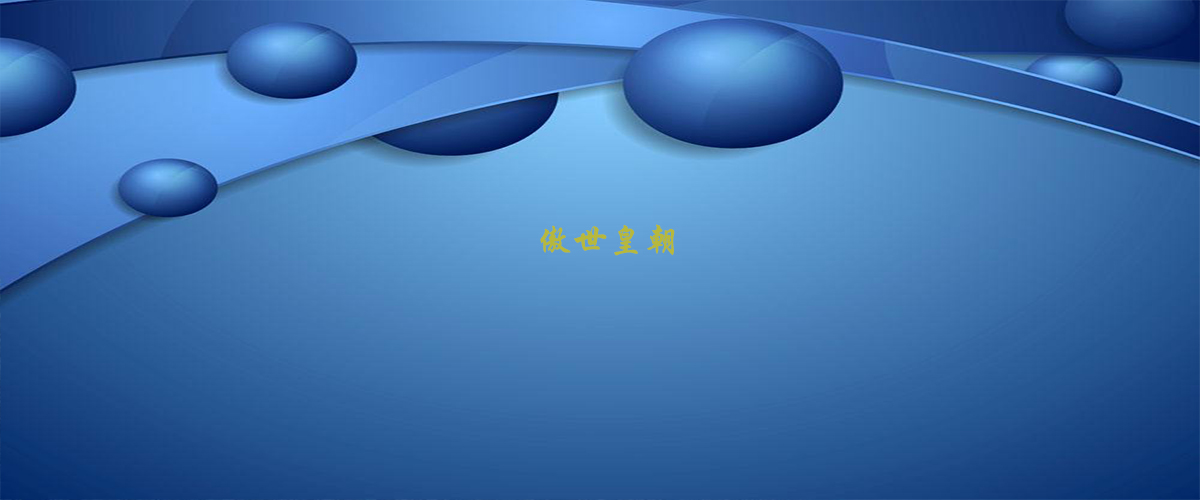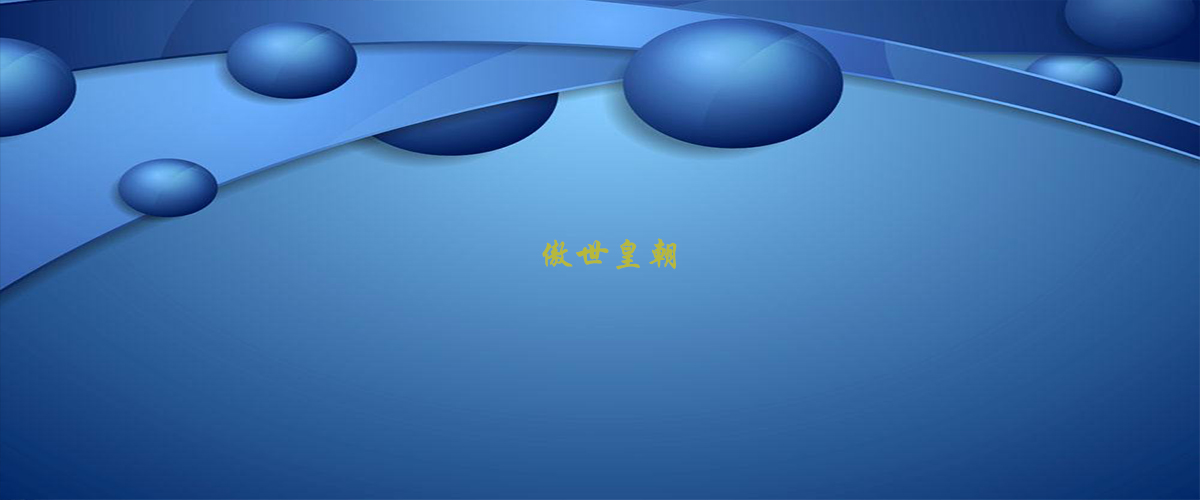傲世皇朝娱乐|《草原》2021年第8期|吴昕孺:大白花蛇
傲世皇朝娱乐平台快讯:
六岁那年九月,我进入老家的罗岭小学发蒙读书。班上坐了二十多个同学,他们都是村子里一窝蜂长大的,唯独我前不久才被爸爸妈妈从外婆家接回来,还没跟他们打成一片,加之年纪最小,就连隔壁宋武都对我爱理不理,这让我非常郁闷。
一天只有五节课,下午三点放学后,我就背着个竹筐去罗岭山上捡柴。
我其实很想跟姐姐一起去捡猪草,但比我大四岁的她有一群自己的玩伴,在家里她还愿意带我玩,一出家门,就把我这只拖油瓶给甩了。我一个人是不能去捡猪草的,因为捡猪草是技术活,要能分辨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有没有毒。妈妈丢给我一个竹筐,说,你去捡柴吧。
那个竹筐可以装得下我的身子。有一次我坐在里面,把自己从堂屋滚到前坪里,被父亲呵斥了一顿。他认为我铁定把那个竹筐搞坏了,但捡起一看,发现没坏,呵斥的声音立时便小了许多。他转身将它挂到堂屋的墙上,我够不着了。
我时常站在下面望着那只竹筐。只是望着它,既不搬凳子,也不搬梯子。如果想方设法,以我的聪明,将它弄下来并不难。但我把这些想法都存放在脑子里,不让它们跑出来。我不是懒——对于玩,我从来不懒;也不是怕父亲骂——反正已经被他们骂得皮糙肉厚了。我只是觉得站在下面望着它,是一件很不赖的事情。
要是妈妈不把它从墙上取下来丢给我,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看着它——它圆圆的身子,围成一张口,不像我们人,身上有很多器官,开了很多口子。竹筐只有一张口,它既是嘴,又是眼、耳、鼻,还是肛门——我对如此简单的器物,抱有一种天然的好感,甚至是崇拜。人就是太麻烦了,吃、听、嗅、拉都要用不同的器官,而不是一个地方搞定。在外婆家,我曾尝试用鼻子吃饭,结果饭没吃进去一粒,倒有半碗撒到地上,被舅妈打了一顿。那次连外婆都不帮我说话,因为浪费粮食她同样不允许,我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科学实验。傲世皇朝登录
捡起竹筐,我做的第一件事,是把自己放进去,从堂屋滚到了前坪。待妈妈从屋里追出来,我已经把它扛在肩上,一溜烟跑远了。一抹风,似乎是妈妈专门派来的,将她的一个声调急促的短语送进我耳朵里:
“小心蛇!”
乡下孩子胆儿大,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一定会怕的,唯独蛇除外。在我的印象中,无论孩子还是大人,没有谁不谈蛇色变。
四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在竹铺上乘凉,耳朵听着大人扯白话,眼皮子却像弹簧片,在上下翻飞。舅妈一口一个哈欠地回了房。外婆用帮我赶蚊子的蒲扇拍着我的腿说,你也去睡。新婚不久的舅舅、舅妈睡正房,我和外婆睡厢房。我揉着眼睛,正要竖起自己,忽然从正房传来舅妈的一串尖叫:傲世皇朝登录
“蛇!蛇!蛇!”
舅舅和外婆冲进屋里。我紧随其后,进到正房时,舅妈正窝在舅舅怀里抖瑟不已,与平时高声大气、怒目金刚的她判若两人。外婆则举起煤油灯,轻手轻脚地围着木床四处查看。舅妈从舅舅怀里抬起头,说话时齿牙都在打颤:
“我刚把煤油灯放在桌上,转身瞧见床上盘着一堆东西,我以为是件衣服,正伸手去拿,那件衣服倏地立起来,原来是一条蛇!一条大白花蛇,好大一条白花蛇!好可怕啊!”
“它去哪儿了?”
“不知道,我都吓晕了。可能从窗户那里爬出去了。”
我非常意外地发现,这个时候的舅妈,柔弱中逗露出几分娇媚,显得格外漂亮。但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她身上,我们都在想着那条蛇。正房的每个角落都查遍了,找不到蛇的踪迹。舅舅用一张牛毛毡将窗户钉得严严实实,舅妈依然不敢上床。最后,外婆要舅舅、舅妈带着我去厢房睡,她自个儿睡在蛇刚刚睡过的床上。我抱着外婆的腿,要是你被蛇吃掉了怎么办?外婆捏着我的脸蛋说,别担心,蛇不会主动咬人,谁欺负了它,它才会咬谁。快去睡吧。
我压根儿睡不着。一来睡在舅舅、舅妈中间,很热;二来我脑子里总在想着那条大白花蛇是什么样子,它是怎样蜷曲在床上,又是如何从窗户缝里溜出去的。我也很担心,那条蛇会再回来,把外婆吃掉。我心里在权衡:与其吃掉外婆,不如吃掉舅妈,外婆多慈爱哦,舅妈又抠又凶……不过,舅妈在舅舅怀里那一闪而过的娇媚,印在了我的心头,我也不忍心让她被蛇吃掉。傲世皇朝登录
此后,我再没见过那娇媚回到舅妈身上,我在外婆家里也始终没见到过蛇。这算得上两桩不小的遗憾吧。
所以,当听到妈妈传过来的那句“小心蛇”,我差点扑哧笑出了声,心里很英雄气概地回了一句:我才不怕碰到蛇呢。
隔壁宋家边上有一条上山的路,这条路直达我们学校,其间有五条岔道通向罗岭山的腹地。我发现,每条岔道口几乎一个模样,都有两三棵枞树、一两棵杉树、几丛檵木和一座坟,坟上大多遗留着几个月前清明扫墓的挂纸,仿佛被定格在那里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。只有第三个岔道右边的那座坟,看不到挂纸,也没有碑,一个圆坑围着一个小土堆,好像是用来种花的盆景,却长满了荒草。风一吹,有挂纸的坟因为被打扫得比较干净,连那些纸都腐朽得动弹不了,这里却风吹草低,而且都是高高的青草,一齐伏下去之后再一齐仰起来,又从另一边伏下去,再仰起来,比我们在学校里做广播体操整齐、潇洒多了。
我在岔路口逗留了很久,还碰见因搞完卫生才回去的学习委员李燕子。她是班上唯一一个对我笑过、和我说过话的女生,那是我有次交作业本给她时,她把我的本子翻了几页,笑着说:“你的字写得蛮工整呀。”平时,我姐总批评我字写不好,“字架子都搭不稳”,那天晚上我一赌气,每个字都是用三角板“画”出来的,结果得到了李燕子的表扬。李燕子跳着走路,书包在她背后蹦跶蹦跶,总像要掉下来的样子,却总不掉下来,让我的心悬着,直到她在我面前停下来。傲世皇朝登录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呀?”
“捡柴。”
“这里哪有柴捡?”
“待会儿去山里,先玩一玩。”
“你一个人玩?”
“是的,一个人。还有风,还有草,还有石子……”说罢,我从地上捡起一枚石子,一甩手,扔进了山里。
“哦,那你好好玩吧,我走了。”
她又蹦跶蹦跶地走了。她住在山那边,走过去应该有六七里远,难道她一直就这样蹦跶回去吗?这个问题我没有多想,我觉得应该进山了。
这条岔道越走越窄,里面的灌木太高、太深,简直像一头巨兽把我吃掉再吐出来,我又被另一头巨兽吃掉再吐出来……走得我的脚有些发软。这个时候,风就不像在外面那般和善、好玩了,而是时常来个恶作剧,冷不丁从背后推你一下,我回头一看,它就没影了,我再走几步,它又来推一下。幸亏阳光尚强劲,透过密集的枝叶,依然能洒落到我身上,给我一些定力和勇气。傲世皇朝登录
终于冲出“巨兽”的重围,来到一片宽敞的平地。平地约有我家前坪那么大,说平是从视觉而言,它没有陡峭的地形,只是从高向低略微倾斜,这里也没有灌木,不知道是被砍光了,还是根本就长不出来。几棵异常高大的枞树拔地而起,枝柯在半空中交织,阳光如水,从尖细、碧绿的枞须间漏下来,形状不一的斑点打在地面铺得厚厚的落叶层上,随风而跳荡、交错,甚至流淌。这里真是一块宝地,有不少现成的被砍断的杉树枝、栎树枝,我还捡到了一个枞树蔸,不一会儿就堆了大半筐。
见时间还早,我捉了一只螳螂在地上玩。不一会儿,又过来一只“铁牛”。在我所了解的昆虫世界,螳螂和铁牛都是很硬气的家伙。螳螂的腿,铁牛的头,是它们防身杀敌的头号武器。恰好我捉到的这只螳螂,腿长而粗,过来的那只铁牛,头大而圆,让它们打起来,岂不是有场好戏看!我便将手里的螳螂放下来,挡住铁牛的去路。
铁牛一愣,没料到从天上跳下个程咬金,连忙刹住几条细腿,晃动着头顶两根触角,好像在报警。螳螂一落地,看到前面赫然有只黑不溜秋的铁牛,也吃了一惊。它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,抬起上身,两条前腿弯曲着悬空,仿佛在示威。它们僵持着,老不打起来。我决定采取激将法,先趴到铁牛那边,用铁牛的口吻对螳螂说:“挡着我铁牛大爷干吗,讨打呀!”接着趴到螳螂那边,模仿螳螂的口气:“明明是你挡了我螳螂将军的路,还不走开,我一脚踩死你!”傲世皇朝登录
它们似乎没有钻进我的圈套,而是同时启动,微微点头致意之后,岔开了身子。我不甘心,赶紧捉了铁牛,又挡住螳螂的去路。只见螳螂扬了扬触须,仿佛在说,别听这小子的,就是他使坏,我们快跑!眨眼间,螳螂纵身一跃,铁牛鼓翅一飞,两个都不见了。
正当我沮丧之际,忽然觉得风吹在背上有些瘆人,我打了一个激灵,才发现太阳已变成夕阳,在慢慢往下跌,天地间陡然阴凉许多。我站起来,拍了拍手,提着竹筐准备回去,瞥见这块平地的最低处、离我十来米远的大枞树下,有一截栎树干,大约因为日晒雨淋,形成了黑白相间的漂亮图案……我欢快地跑过去,弯腰捡起——那截树干隐藏在落叶中的部分竟然很长,而且是黏滑的,更关键的是,它还能动!
蓦地,一道惊悚的闪电莫名掠过我的全身,我慌忙将手中的“树干”奋力扔了出去。然而,它却落在离我很近的地方,半个身子直立起来,和我差不多高,三角形脑袋上的一双锐眼,无比恼怒地瞪视着我,嘴里吐出半寸长的芯子。我两只手缩在胸前,全身抖成筛子,连哭都忘了,两腿间膀胱一紧,一泡尿冒了出来,幸好有裤子挡着。傲世皇朝登录
虽然从没见过,但我当然明白它是一条蛇,而且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白花蛇。我脑海里只有这个唯一的意识了,其他都是空白。我的魂已经丢到了九霄云外,不知道是否去了外婆家。是的,真的去了外婆家,在那间正房里,一条大白花蛇蜷曲在床中间。我在想,如果它硬要吃掉一个人,究竟是吃掉外婆呢,还是吃掉舅妈?这下有答案了,它要吃掉的是我。
尿完了,我又打了个激灵,意识稍稍清醒,恐惧霎时将我严严实实地罩住,我绝望得想要号啕大哭,嘴巴的弧度都张开了。这时,几乎逼到我鼻子前的那个三角形脑袋倏忽矮了下去,眼里的凶光亦和顺几分;接着再矮了一下;第三下,它就和自己的身子差不多平行了。它依然看着我,在空中转了两个圈,是在跟我打招呼吗?我还没回过神,这条长得超乎我想象的白花蛇扭转头,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向一丛深草中滑去。它像一条河,像一束光,像一列梦想中的火车。
即将滑出我视野的时候,蛇尾在落叶上疾速扭动,酷似一圈圈曼妙的涟漪。我相信,它是故意那样的,因为它知道我还待在原地。
又过了一阵,尿湿的裤子凉人了。我背起竹筐,摇摇晃晃走到来的那条岔道上,突然像发了神经一样猛跑起来,一口气冲进了家里。妈妈看我那样子,问道,出什么事啦,有狗在后面追啊?我说,不是狗,是蛇,一条大白花蛇,好大一条白花蛇!妈妈闻到了我身上的尿臊味,她声调不高,却含有愠怒:“还说是蛇在后面追,是条‘尿蛇’吧!再贪玩,撒尿的时间总要留出来啊!这么大的人,还尿在裤子上,羞不羞?这条裤子你自己去洗。”傲世皇朝登录
妈妈可比舅妈温柔多了。舅妈太喜欢骂人,但她骂了之后不会要我去洗衣、洗碗,这些事她都会做得妥妥帖帖。妈妈不太骂人,不过我自己玩脏的衣裤得自己洗,吃饭拖在后面还要洗碗,也蛮烦人的。
我洗完裤子,妈妈表扬我今天捡柴的成绩不错,相比之下,姐姐的猪菜篮里就显得单薄了。我缓过劲来,心里琢磨着那条白花蛇,它竟然不咬我,是不是也怕我呢?这么一想,顿时生发出一股英雄豪迈之气,便跑到堂屋,绘声绘色地给妈妈和姐姐讲起我是如何遇到一条大白花蛇的。姐姐听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,她认为我是在故意吓唬她,以报复她前天晚上没带我出去玩。看得出,妈妈也不怎么相信,她只是肯定我故事讲得好。
我家房子和宋武家一样,紧靠着山,他家那边还有一条去学校的路,我家这边连路都没有,靠山靠得更紧。宋武家的屋和山之间,被他父亲挖出一个小院子,种上了桃树和橘树。而我家,屋和山之间仅有一口水井,在外教书的父亲便也效仿武家,每逢节假日和星期天,就在后面挖山,想拓个院子出来。傲世皇朝登录
我们和宋家,隔着一条塍,是宋武的父亲宋天奇挖山时堆起来的。我父亲吴自强就将他挖出来的土,顺着那条塍往前堆,一直堆到我们屋前的路边上,形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分界线。宋天奇对我父亲的这个工程颇感兴趣,时常过来帮忙。这样,宋武也过来得多,我们渐渐玩到一起了。
在我巧遇大白花蛇两个月后,时令已入深秋,但那年温热干燥,立秋之后没下过一滴雨,白天两件衣服都穿不住。我父亲得意地说,老天有眼,这么好的天气,是要让我今年完工。他干得非常卖劲,我家后院也越来越成形。
有个星期六,父亲特意请了半天假,骑着自行车早早回到家里,他要解决“后院”的最后一道难关——一棵看上去低矮而蓬松、像一顶破帽子的榆树,其根系却异常发达,而且卡在顽石崚嶒的崖壁间,周围差不多掏空了,它还巍然矗立着,不倒下来。父亲准备放弃算了,但宋天奇说,这棵树卡在这里很难看,再想办法撬掉几块石头就没问题了。父亲觉得也是。他们搭着木梯,用锤子将铁钎敲进每一条能够看见的榆树根的缝隙,并将那些细一些的树根用凿子斩断。
一个时辰之后,榆树明显开始倾斜,根部不时发出“咔嚓”的断裂声。他们将一条粗麻绳搭在树蔸上,两人下了木梯,一人手里攥着麻绳的一头,嘴里吆喝着,一齐使劲往下拉。我和姐姐,还有宋武和他妹妹宋霞,一字排开在我家后墙根下,观摩着这场难得的大戏。傲世皇朝登录
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榆树倒了下来。我们感觉,整个山都塌了半边!在绿色的树枝和黄色的泥石之间,还有一道黑白相间的闪电,它像一条龙在半空中矫捷地舞动,然后重重地落在地上。它正要往倒在旁边的那棵榆树的枝叶里钻,被眼疾手快的宋天奇抓住尾巴揪了出来。它昂着头,回身朝宋天奇扑来。宋天奇毫不慌乱,抓着它抖几抖,它的头立不起来,索性向下俯冲,去咬宋天奇的脚。宋天奇这下惊得手一松,高喊,是条白花蛇,大白花蛇,快拿锄头来!我的知识分子父亲从杂屋里拿出锄头,却不敢上前。宋武的父亲从我父亲手里抢过锄头,连续下砸的锄头,让白花蛇既无法逃脱,又无力进攻。
突然,它像是蓄足了气力,半个身子直立起来。宋天奇不敢大意,身子往后一缩。但它的三角形脑袋并没有吐出芯子去攻击宋天奇,而是朝着我站的位置偏过来,定定地看着我,眼光里充满了令人心疼不已的哀伤。我幡然明白,它就是我上次捡柴时看到的那条白花蛇!
“宋伯伯,不要打它!”
我冲上去要抢宋天奇手里的锄头,被宋武拦住,姐姐也使劲拽着我。我不停地哭喊:“住手,这是我的蛇,这是我的蛇!”傲世皇朝登录
等宋武那小子松开我,大白花蛇已经在地上瘫成了一堆。宋天奇最后一下狠狠地砸在了它的七寸上。他把它捡起来。他手里那长长的一线,像一条枯竭的河,像一束被吞噬的光,像一列梦想中翻倒了的火车。
宋武很不屑地睃我一眼:“看到我爸要把蛇打死了,你就说是你的,羞不羞啊!”
宋天奇对他儿子说:“是在小宇家里打的,当然也是他的。”
我父亲大概也从一场梦中醒来了,他连忙说:“不要,不要,我们家不吃蛇的,你们拿去吧。”
宋天奇拿着那条蛇,像个得胜回朝的将军,后面跟着他的儿子宋武、女儿宋霞。
姐姐觉得我刚才丢了丑,她不理我,出去玩了。我只是哭,一个人哭。妈妈从外面回来,问是怎么回事。父亲说,还不是争一条蛇。我高声喊道,我不是争,那就是我的蛇,他们打死了我的蛇!妈妈把我拉到房里,要我平静下来,我便一边啜泣,一边跟她诉说。
妈妈听得眼眶发红,但她没有作声,没有说一句话,只是摸了摸我的头,去厨房做饭了。
快吃晚饭的时候,宋霞端了一大碗汤过来,放在我家桌上说:“这是蛇汤,喷香的,我爸要我送一碗过来。”我像只老虎一样罩过去,从宋霞手里接了那碗汤,全部倒进潲水桶里,然后把碗塞给她。她委屈地嘟着嘴跑回去了。傲世皇朝登录
父亲腾地起身,抓根竹条就要抽我,被妈妈制止了。妈妈弯下身子对我说:“小宇,很对不起,当你两个月前告诉我,你捡柴时看到了一条大白花蛇,我当时并没有相信你。现在,我不仅相信那天你看到了一条大白花蛇,而且我还相信,今天他们打死的大白花蛇就是你那天看到的那条。”
夜深了。月亮没有出来,星星也没有出来,夜却不是那般黑,而是从那暗黑里,渗出丝丝白光,构建成黑白相间的漂亮图案。这迷离的深夜,好像有着自己的躯体,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,让人难以察觉地扭动着、滑行着。
【吴昕孺,本名吴新宇,湖南长沙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长诗《原野》、散文集《边读边发呆》、随笔集《心的深处有个宇宙——在现代诗中醒来》、中篇小说《牛本纪》、长篇小说《千年之痒》等20余部。现供职于湖南教育报刊集团。】
傲世皇朝平台:www.jhc10086.or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