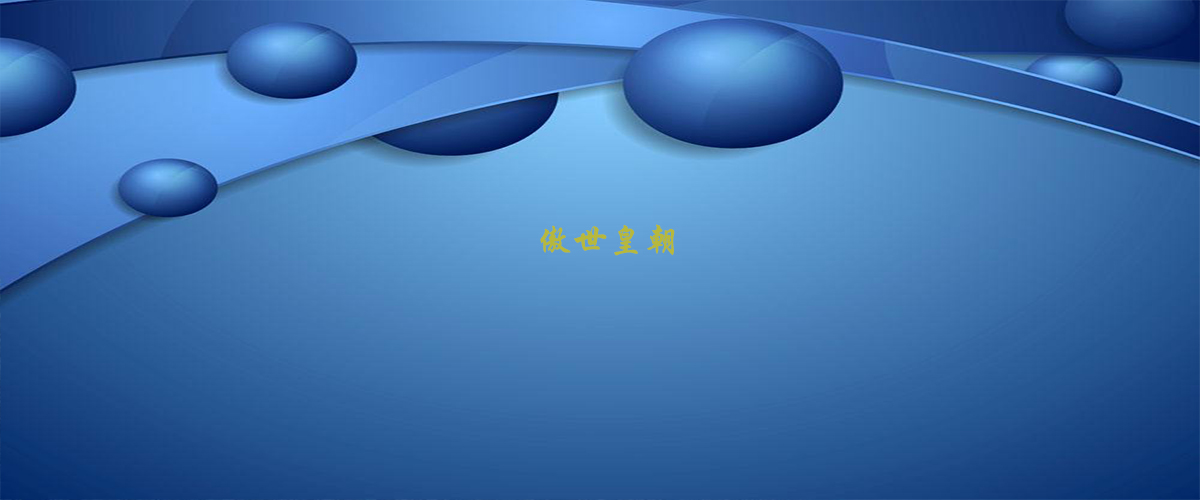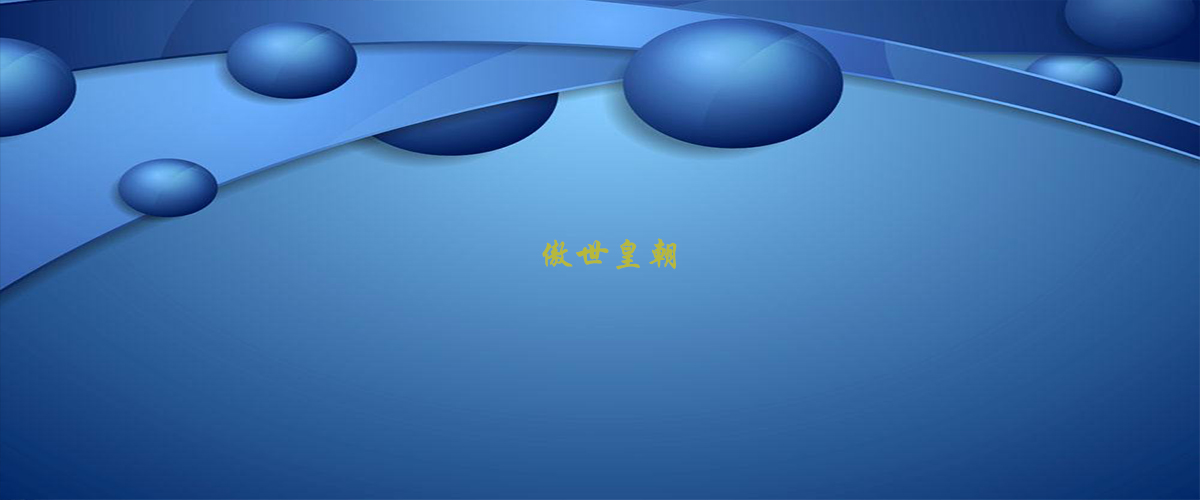傲世皇朝娱乐平台注册|《当代人》2022年第7期|人邻:十九棵桐树的医院
傲世皇朝注册报道:
1
老人说,这边先前是很大一片树林,多的是桐树,因铁路南边扩建,铺排多条铁路,于是将树砍了。铁路北边,要建医院,有人说,可惜了,有绿荫多好,才留下了这些桐树。
医院,叫兰西医院,说全了是兰西铁路医院。住院部南面,是这些留下的桐树。医院离家里先前住的平房不远,夜里静,能听见火车经过的声音,“咯噔、咯噔”。那时铁道上铺的是二十五米的短轨,接缝那儿,几秒钟就会“咯噔、咯噔,咯噔、咯噔”,一节节车厢的两组车轮从接缝先后轧过,很有节奏。火车过去,远了,远了,“咯噔、咯噔,咯噔、咯噔”,听不见了,耳朵里习惯了,好像还有“咯噔、咯噔”的声音。
后来家搬到六号楼,跟铁道更近,夜里,火车的声音更大,好在那时候小,无所谓失眠,一夜睡得沉沉的。
小孩子贪玩,那些年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少,下午只两节课,回家一会儿就写完了。也有时候,在教室里写,几个孩子早上就约好了去哪儿玩。轮着大扫除的几个同学,急慌慌扫着,“呼啦、呼啦”,扬的满教室灰尘,这边挪一下位置,再挪一下,不及坐下,就那么趴在课桌上,挪着,把作业写完了。
玩的地方,是分局,铁路分局,偶尔去,那地方有人看门,得小心着,从传达室的窗子下面,猫着腰偷偷进去。想进去,是因为二楼的会议室里,有好的乒乓球桌,红双喜的,还有网子。学校的,是水泥台子,网子,是排成一溜的几块砖头。
更喜欢的是医院,大门敞着,没人管,地方也宽敞,是玩耍的好去处。一进医院的大门,远远就能看见那一片桐树。有时候约着去医院,不说医院,是说几点到桐树那儿碰头。
去医院是找输液的橡胶管,医用废弃物的箱子里,不时会有护士丢弃的。那时的输液管是纯橡胶的,虽然丢弃的稍稍有些老化,可弹性是够的,比起自行车内胎,用输液管做拉条的弹弓,拉开了更有劲。洗干净的输液管,剪成一尺长的两截,用细铁丝系在弹弓把上,另一头缀上一小块包皮,要是有一块牛皮就更好。有一把这样的弹弓,要神气好多天。怕大孩子抢,小孩子藏在裤兜里。可即便这样,脸上也掩不住。见一个大孩子,尤其是顽劣的,赶紧躲着,低着头沿着墙根走,脸上紧藏着的喜气还是给人看出来。不敢搭话,抽空子就跑,还是跑不及,给人揪住。诘问,跑什么?一边说,没什么,一边不由自主地扭着腿,捂着裤兜。这下就糟了,人家逼着,从兜里把弹弓强掏了出来,顺手用弹弓在小孩子头上脸上摔打几下,就这个,还藏着,上车了。上车了,是那时候铁路上的孩子“归了我”的意思。
大孩子吹着口哨,腆着没有肚子的肚子,扬长而去。傲世皇朝娱乐登录
弹弓没了,沮丧地连着几天去医院,废弃物的箱子里,翻翻,什么也没有。
路过桐树林,对着一棵,泄恨一样踢一脚,踢得脚生疼,赶紧脱了鞋,抱着脚揉搓,嘴里骂一句。郁闷地待一会儿,忿忿地看着桐树,心想,等老子长高了。等着。
2
那时的医院,也都有太平间。一早上学,从六号楼到学校,要下一个陡坡,往南再过一个桥洞才能到。桥洞的灯也昏暗,就有些阴森森,不愿意走那儿。尤其是冬天,七点过了,天还没亮,黑黢黢的。也冷。过桥洞就更冷。不走,就得从陡坡上面走,去学校也近一些,可这就要经过医院西北角的外墙。西北角有医院的太平间,为了忌讳,也为着出殡方便,朝外开着一个门。
太平间门口,吊着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,灯罩的遮挡,只是照着前面地上的一点亮,太平间的半个门,还是在黑暗中。尽管走了很多次,经过那儿,心里总还是有点害怕。壮着胆子,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去,手里攥着石头什么的,没有,就紧紧抓着书包,眼睛盯着,生怕那扇门,人经过时忽然有什么响动。也有时遇到同学,两个人伺跟着一起走,胆子就大一些。待走过去,手里的石头瓦块没用了,松一口气,又转回来,“咚”的一下打在太平间的门上。门一响,人就飞快地跑了,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有时候看前面走着谁,悄悄跟在后面,等他刚刚走到太平间门口,“咚”地一下把石头打在门上,那人一下跳起来,“妈”的一声,几乎要跌倒。若是女孩子,还带着哭声。
这太平间,是进过一次的。好像是初一时候。一天后半夜,邻居孩子一个叫天福的忽然敲门。人睡得迷迷糊糊,只听外面喊,我是天福,我奶奶不行了。
天福的父亲是上过朝鲜的荣誉军人,腿脚不便。我父亲好像因单位值班,不在家,我只好匆忙起来,跟着天福到他家。不知是谁,已经从哪里弄来一副简易担架,我跟天福俩人抬着天福奶奶就往医院赶。到医院大厅,还没有进急诊室,一个医生听见声音,从里面出来,翻看一下天福奶奶的眼皮,大约是瞳孔已经扩散了,又听听心脏,说,不行了,人走了,抬太平间去吧。
有人一会儿拿来太平间的钥匙,前面去开了门,站在门外,等着我和天福抬着天福奶奶进去。不巧的是,我抬着前面,就只能先进去。太平间有点冷,荧光的灯管,光也是冷的。我抬着天福奶奶走在前面,不敢往两边看,可还是忍不住紧张地悄悄往两边瞥着,生怕哪一个死人忽然出了口气,活了过来。我屏住气,不敢呼吸,憋得有点胸口疼,祈盼赶紧有一个空的格子,好把人抬进去,赶紧出去,逃出去。外面的几个格子里面的水泥台子上都有人,身上苫着白布。害怕,可还是得往里,左右一间一间看,哪里有空的。有的,好像小巧一些,也许是女人。也看见一块白色的布单下,苫着一个人,是男人,露出苍白的裸着的两只脚。傲世皇朝娱乐登录
太平间不大,左右各有三个格子。左边的三个格子都有人,右边的,只有最里面的一个空着。到了格子口,我在前面,也只能先进去。怎么进去的,怎么将天福奶奶从担架上抬下来,挪到里面的水泥台子上,我都忘了。担架上似乎还带了一块什么布的单子,不是白的,可颜色我忘了,赶紧盖在天福奶奶身上,脚好像都没有遮严,就慌乱出来了。
去的时候,我们是三个人,尽管天福奶奶是躺在担架上,回来,成两个人了。两个人抬着空的担架,谁也不说话,不难过,似乎也不沮丧,就是木然的样子。经过住院部一边,那一片桐树映着月色,朦朦胧胧的,一棵棵立着,默不作声。刚刚的忙乱,忽然安静下来,才忽地觉出累了,觉出额上的汗冰凉,觉出刚刚抬过担架的手臂,有些酸胀了。攥一下手,手里还抓着担架,上面却空着,一个人就这样,说没就没了。
那样结实的脚,暴露在太平间青白荧光下的,我后来再没看见过。那样的气氛,苍白而冰冷的,孤独的死亡,也只是在挪威画家蒙克的画里看到过。
现在想,那个夜晚,无意识间,那一大片桐树,是给了我心里潜在的安慰的。虽然它们默默立着,虽然我没有直接的感觉到。毕竟,那是生的力量,一大群的生的力量,虽然在夜色里沉默着。
3
那时候看病,跟现在不大一样,大夫写了处方,去药房拿药,药房都是按照三天五天的量,用小勺在一个药瓶里舀出来,几粒几粒,数清楚了,倒在很小的纸的药袋子里。药片倒进纸袋的声音,“嚓啦、嚓啦”,无端地觉得好听。似乎听听那声音,病就快好了。
这样的纸袋子,母亲还糊过。一年,也并不全然是为了生计,反正是母亲闲着,邻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给这家医院加工的手工活儿——糊纸药袋子。药袋子是裁好的一摞摞长方形纸片,一侧和下面多出一个边。糊的时候,将一小叠纸片在桌子上蹲齐,斜着四十五度角,搓扑克牌一样,用手指慢慢搓开。等那两个边均匀露出来,一手捏紧,一手用刷子蘸了浆糊,将那两个边刷好。将纸片对折,再将刷好浆糊的两个边小心折过去,粘好,顺着摁一下,一个药袋子就糊好了。
去医院看病,药剂师给药的时候,看着药袋子,偶尔会想,这个药袋子说不定就是母亲糊的那一个。
多年后,收拾家里,偶尔还会在哪里发现以前用过的旧药袋子。药已经吃完了,可那个纸袋子还好好的。正面是手写的药名和服法,一天几次,一次几片,空腹还是饭后。那时候,医生和药剂师都是用那种木杆的蘸笔,在墨水瓶里蘸一下,写几行字,蘸一下,再写。拿起药袋子,闻闻,袋子里的药味,还带着人的体温一样,若有若无。那蓝墨水微微呛鼻子的气息,也似乎还在。傲世皇朝娱乐登录
母亲住院,因为近,更因为是铁路家属,免费,总是住在这家医院。母亲八十以后,体衰多病,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。一次住院,我下楼打开水,回来见母亲站在开着的窗子边。听到我的脚步声,母亲回头,有些奇怪地笑笑,对我说,从这儿跳下去,一切都省事了。
我探头看看,这是二楼,窗子下面有一个平台。我笑笑,你跳下去也没用。有个台子。再说,我认真起来,你这样走了,邻居怎么说我们?
母亲说,也是。
母亲住的是套间。正说闲话,忽然听见外间有窸窸窣窣的声音,我出来看看,是隔壁的病人,有些糊涂的,正转身往外走。看看他手里空着,也就不管。到这样年纪,糊涂了,就没有了生死。母亲再老一些,也该是这样。再老一些,就不会想到麻烦我们,想到死,想到死了以后的我们。
进去,母亲还在窗口站着,却是看着那些桐树。母亲的老家,外婆家院子里,也有这样一棵桐树。桐树旁边,是一口水质清澈的井。
八十多的母亲,她最后的日子,也许是在家里,可也许是在这家医院里。她走的时候,那些桐树也都会是默默的,有如送别。
4
这医院,也自然是父亲住院的地方。多年来,父亲几乎没有生过大病。老了,八十六了,去年一年,却连续住院,竟然至于七八次之多。夜里,火车经过的噪声,“咯噔、咯噔”,父亲睡得很沉。在铁道附近住了很多年,父亲听了多年的车轮声,习惯了。据说,还有这边的人搬到安静地方,夜里听不见火车声,反而难以入睡。
多年来,父亲是固执的。父母去世早,他一个孤儿,也许,只能如此。检查骨密度,说老人的骨密度不错,这个年龄少见。他骨头的密度也将好相合于人的倔强。但他已经没有了力气,起来的时候,已经有些吃力了,手要尽力撑着。拍胸片的时候,父亲按着医嘱把胸口紧紧贴在那块金属的板子上,鼻子几乎给挤扁。那一会儿,父亲一点也不固执,他知道那是医生,违碍不得。
知道肯定是小脑萎缩,可还是做了CT,脑部扫描一下。父亲的背已经驼了,躺在扫描床上,他的头因为驼背而前倾,虽然尽量向后仰着,还是够不到枕着的位置。无奈,我脱去棉背心,卷起来垫在他头下,才勉强躺下了。看着仪器的扫描,清晰地显现着父亲白色的头骨。看过日本的片子《洗骨》,家人会在亡者过世的第四年,将亡人的骨头从临时安葬的地方取出,清洗干净了,再一次祭拜,才最后安葬了。看着父亲的头骨,知道用不了很久,也许两年,也许再多一两年,离开人世的父亲,最终也会是这样,随着时间消失了那些多余的组织,仅仅剩下这些仪器扫描下的白骨。我看着,近乎虔敬,心想,若干年以后,不惟父亲,自己也会是这样的裸露的头骨,虚妄地坚持着,好像不肯泯灭。傲世皇朝娱乐登录
夜里,随着父亲的稍微一动,睡不踏实,就转头看看,父亲又安静下来了。父亲睡着了么?可能。可也好像父亲并没有睡得太沉。一会儿,父亲完全不动了,坚持一会儿,忍不住还是起来看看。没开灯,贴近了,听见父亲微微的呼吸,才放心了。假若父亲真的在睡梦中走了,安详地走了,也就走了吧。八十六,也算是高寿了。我的爷爷奶奶都走得早,我没见过。比起他们去世的三四十岁,父亲是高寿了。父亲早逝的父母,不会想到自己的孩子竟然活了那么久,还竟然是在离洛阳那么远的一座城市,他们人老几辈都陌生,百余年前是流放地的大西北。
小弟送饭来,父亲衰弱,可饭量还是不错,大口地吃着炖得很烂的肘子。手哆嗦着,已经用不好筷子了。给他拿了勺子,可他固执。用了一辈子筷子了,他不习惯。早上起来,鞋,也笨拙地穿不上了。想起他年轻时候,不到三十的样子,在老家的火车站,那么年轻,甚至是有些英俊,那么有活力。现在他的腰弓着,眼神迟滞茫然,偶尔还会有幻觉,忽然间指着地下,用手去抓,说是有乱爬的什么虫子。
医院的院子里,走走,秋风起了,那一片桐树,十九棵桐树,树叶“哗哗”响着,在风中愈显得高大。一棵桐树,奇怪地一块树皮没有,裸着,以为是什么碰的,却不是,那裸着一块不知为什么竟然像是一个人形,像是刚刚进去,也像是一个人正要走出来。
5
这几年,托小弟的福,父母搬到西站一个新建的小区。依旧离铁道不远,六楼,站在窗子前面,可以看见铁道这边的医院。
前几天回去,父亲说,有消息说,兰西医院要搬迁了。说是要在榆中那边建设一个两千张床位的大医院。
搬迁?这边呢?
可父亲言之凿凿。老了,就更是。除了固执,更是有些糊涂了。固执加糊涂,说话就没有余地。
六楼的窗前站着,看着,医院的太平间早没有了。医院西南边,是后来盖的门诊楼。那个陡坡也没了,是进出医院门诊楼上下的台阶,再就是有一条长的坡道,供汽车进出。
也许,这一切真的要过去了。可即便是过去,是医院作为一个物过去了,而那些记忆还在。
医院,也许是要拆了。消息更近了。新建的,也许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。这边拆了,也许会重新再建一所。现在的医院,尽管后来有翻建,有新建,但毕竟是太老太旧的狭小医院。这边有很多人居住,需要一个医院,哪怕不够大。傲世皇朝娱乐登录
医院要拆了,这些桐树呢?这块地方,他们要做什么用?有用的话,这些无辜的树也许就给毁了。
好些年了,这些树也不知是哪一年,不知是什么人种下的。荫庇着住院部的这些桐树,很多年,在我的眼里似乎再没有长过。太过高大的树,也许很难看出它们的生长,不过是年年岁岁,新叶长出来,大了,满是绿,而后枯黄了,秋风里,飒飒落了。
小时候,我跟小伙伴数过这些树。不成行的树,不好数,数着数着,树似乎会旋转一样,每一棵树也似乎都长得一样,转着数,数着数着,就乱了。记得几次都没有数清楚,只得捡来一些石子,数一棵,放一颗石子,才终于数清。一共十九棵。
这些桐树如果一直会在,让它们安安静静长着,多年后该是什么样子呢?我查了一下,这种树,是梧桐,寿命可达百年。百年之后,才会空心,干枯,死去。
想想,人也一样。
又想,医院若真的拆了,这条东西的铁路动脉还是在的。火车的声音还在。车轮的声音,过去,消失,静了下来。有心的人,长夜不寐的人,会在那宁静里,想起一些难忘,永不会磨灭的,就像是沃伦在他那首诗《世事沧桑话鸟鸣》写的一样——
那是一只鸟在夜晚鸣叫,认不出什么鸟/当我从水边取水回来,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/我站得那么静,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。
多少年过去,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,有的人已谢世/而我站在远方,夜,那么静,我终于肯定/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事物, 而是鸟鸣时的那种宁静。
那种宁静里,看似空空的宁静里,真的,一切都在。诗人沃伦怀念的那些终将消逝的,都在鸟鸣时的宁静里安顿着。
那些桐树呢,不论它们何时消逝,也都会在无限的宁静里,给人记着。即便记着它的人,也随着时间,在风中消逝。
人邻,河南洛阳老城人。出版诗集《白纸上的风景》《最后的美》《晚安》,散文集《闲情偶拾》《桑麻之野》《找食儿》《行旅书》,评传《百年巨匠齐白石》《李清照》《江文湛评传》等。
傲世皇朝登录:www.jhc10086.org
下一篇:傲世皇朝注册|过好这一生